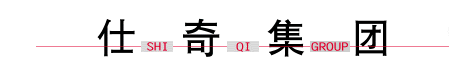|
试论蒙元时期的蒙古族萨满文化
色 音
(中国民族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本文使用《蒙古秘史》等蒙语文献史料和手抄本,借鉴中外学者的相关成果,同时利用现代田野调查资料,研究元代蒙古族萨满文化,分析其原生宗教的内容、形式和发展演变轨迹。
[关键词]:元代;蒙古秘史;萨满教;原生宗教;祖先崇拜
近年中外学者对萨满教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但对元代蒙古族萨满教的研究还不多,本文主要利用《蒙古秘史》等蒙语文献,同时参考其他文献,并利用田野资料,对蒙古族的萨满教进行研究,指出其本民族族原生态宗教的特征,并对其后世变迁进行分析。
元代是蒙古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转折期,萨满教在其中起到相当的作用。忽必烈汗建立元朝,登基皇位后,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祭祀祖先的盛典。《元史》卷七十七载,元朝每年8月28日在大都(北京)举行祭典,跪拜呼唤成吉思汗名。蒙古族萨满教中的祖先崇拜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祭祖活动是蒙古萨满教祭祀仪式的重要内容。据古代文献记载,祭祖“由珊蛮(即萨满)一人面向北大声呼成吉思汗及诸故汗名,洒马乳于地以祭”。这一古老的信仰习俗,在今天的内蒙古地区祖先崇拜活动中仍有遗踪可寻。如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成吉思汗祭典以及东部科尔沁萨满的祖先崇拜活动等都是较具代表性的。另外,散居世界各地的其他蒙古各宗也有保持祭祖传统的。如,云南蒙古族的家庭中,供奉灶君,“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和祖先的牌位。有时扎制偶像,拥抬游村。
传至今天的蒙古族祭祖活动中成吉思汗祭典是比较完整地保存古老传统的祭祖形态。成吉思汗祭典的成例,自窝阔台汗时代即已开始。到了忽必烈建立元朝,登基继承皇位以后,在大都(今北京)举行大规模的祭祀祖先盛典,并规定了祭祀成吉思汗的“四时大祭”。《元史》等古代文献中都记有成吉思汗祭典的内容。成吉思汗祭典包括平时的瞻仰性祭祀,每月的礼祭、正月(春节)大祭以及四季祭典等祭祀仪式。
在蒙古民族的战争史上,萨满教也起过重要作用。据《蒙鞑备录》载:“凡占卜吉凶,进退杀伐,每用羊骨。……类龟卜也。”《黑鞑事略》也云,古代蒙古人“其占筮,则灼羊之枚子骨。验其文理之逆顺而辨其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信之甚笃。谓之烧琵琶。……每将出征,必令公预卜吉凶,上亦烧羊髀骨以符之。”萨满教的日月崇拜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产生的原始直观的天文知识也被广泛地运用在军事活动中,并与占卜习俗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蒙古族早期军事活动中以天象观测来决定兴兵与否的重要依据。这和古代中原帝王们战争中广泛运用充满神秘主义的祥瑞预兆颇为相似。这种以占卜预兆来决定军事方案的宗教神秘主义做法在早期的战争中也有一定的积极功能。占卜的结果往往成为采取某种果断的军事行动之重要依据,这比犹豫不决中被战败或进入被动局面要好得多。尤其积累多次的战争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天文占验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时“占卜者们宣布有利或不利于进行各种事情的日子。因此,除非他们同意,蒙古人从来不进行军事演习或出发作战”。在信仰萨满教的少数民族的军事史上,萨满巫师根据各种奇异天象而总结出来的天象占卜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北方民族的古代天文学正是在军事占星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黑鞑事略》载,古代蒙古人“择日行事则视月盈亏以为进止,月出之前,下弦之后皆其所忌。”《心史·大义略叙》也记载,古代蒙古军队“秋出兵,春休兵,岁岁验中秋夜月明为利,即兴兵;若中秋夜风雨晦冥为不利,即不兴兵。”这里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月明则可正确判断敌情,而月冥则无法正确估计敌方的军事力量和战斗布局而容易被战败, 这可能是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知识。鲁布鲁克在他的游记中曾写道,13世纪蒙古占卜者中“有些人熟悉天文学,特别是他们的首领,他们预言日蚀和月蚀的时间。当日蚀或月蚀将发生时,所有的人们都贮藏食物,以便届时不需走出家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萨满巫师是北方民族军事天文学的开创者,而正是在萨满巫师们开创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军事天文学中孕育出北方民族科学天文学的萌芽。
在古代北方民族中流行的呼风唤雨的法术和民俗技巧后来基本上被萨满巫师和占卜者垄断了。据《黑鞑事略》载,12世纪时蒙古人“无雪则磨石而祷天。”当时掌握致风雨术的好像不仅仅是萨满巫师,一般民众也会此术。而到了13世纪蒙古帝国时期和元朝时期,这种法术已基本上被萨满巫师和占卜师所独占了。13世纪时到过蒙古地区的普兰·加宾尼在游记中说:“占卜者们也要用他们的咒语来扰乱气候。”《马可·波罗游记》也载,忽必烈汗所重用的占卜者中有些人能够呼风唤雨。古代蒙古族占星家们不仅能够呼风唤雨,还能够灵活运用此术来控制天象、扰乱气候。
萨满巫师和占卜师所用灵石往往取自动物腹中。方观承《从军杂记》载:“蒙古、西域祈雨以楂达石浸水中,咒之,辄验。楂达生驼羊腹中,圆者如卵,扁者如虎胫,在肾似鹦鹉嘴者良。色有黄白。驼羊有则渐羸瘁,生剖得者尤灵。”《黑鞑事略》又载:“蒙古人有能祈雨者,辄以石子数枚浸于水盆中玩弄,口念咒语,多获应验。石子名曰‘ 酢嗒’,乃是走兽腹中之石。”以灵石祈雨的巫术在有些蒙古地区至今仍有遗存。在民间传说中,这类巫术习俗往往以呼风唤雨的母题表现出来。尤其在蒙古族英雄史诗中,当主人公在战场上借助呼风唤雨术来战胜恶魔蟒古思的情节母题,与萨满的札达术密切相关。
北方少数民族军事首领们不仅在战场上广泛使用萨满巫术,在战争开始前或结束后也要举行一些萨满仪式。有时候甚至在萨满教仪式活动上讨论决定军事策略。出征前祭战旗即军 的祭祀活动与萨满教观念有关。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征讨乃蛮部时,由于乃蛮部兵力众多地势有利,成吉思汗为鼓励战士们的战斗勇气,唤起他们的战斗力,“鼠儿年四月十六日”祭了旗纛,去征乃蛮,结果成吉思汗大胜。这是一种精神战术。战旗不仅是统一行动的战争符号,同时起到了唤起战斗力的暗示符号作用。《蒙古秘史》又载:“子年(1204年)夏初月三十六日,既望之时,祭旗出征也。”在现今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中祭奠的神矛就代表着战争的旗徵,所以,成吉思汗的镇远黑纛,也叫四游神矛。战旗和神矛往往成为一体。成吉思汗在战场上往往以祭战旗的方式来唤起蒙古军民的战斗力,使他们团结在战旗之下发挥出目标一致、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战旗在成吉思汗的历次战争中起了统一军民思想和行动的作用,同时也起到识别敌我双方,防止内部残杀的标识作用。
古今中外的战争实践证明,任何战争都需要一个统一军队思想和行动的符号系统,而人类早期战争中宗教往往成为神圣的战争符号。祭旗出征的战争仪式就是这种宗教符号系统发挥其作用的具体方式。在战场上战旗往往成为骑士之神,勇敢的骑士们团结在神圣的战旗之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力量,这样战旗成为激发集体力量的催化剂。战神崇拜和战旗的崇拜密切联系在一起,更能够调动战士的战斗热情和所向无敌的战斗勇气。信仰萨满教的诸民族之观念中,战神被认为居于战旗中,战旗是保护军队的守护神,是决定胜败的力量源泉。据德国蒙古学家海西希的研究,在对成吉思汗崇拜的范围内,要在特定的时间内为黑纛、白纛和彩纛组织祭祀活动,与此有关的祈祷文也都保留下来了。在萨满教信仰中,战旗和战神往往被联系在一起。蒙古萨满教天神系统中专管战旗的天神叫苏勒德腾格里,而专管战争的天神叫戴沁腾格里。
祭战旗和战神往往有相应的祭词祷文。蒙古族祭战旗的祝福仪式中唱道:
仁慈的腾格里战神,
请享用吃喝,
让我们洒下乌巴什珲台吉的黑血。
在萨满教祭祀苏勒得腾格里的祭词中所描绘的战神形象为:
你是苏勒得腾格里神,共有九兄弟,
放射出了白色和红色的光芒,
骑上的纯种烈性马。
头戴大桶式的盔,
身穿黄皮甲帽,
脚蹬长筒靴。
身佩虎皮箭囊和豹马弓套,
腰缠护腰,佩有短刀和宝剑,
手执三根苇棒。
头上有雄鹰翱翔,
右肩上有一只狮子俯卧,
左肩上有一只老虎跳跃,
两侧有黑犬、黑熊和黄熊。
……
战神祭词中往往绘声绘色地描述战神的形象,并向它祈祷、请求、甚至立盟誓,以此来表达战胜敌人的决心。战争中的盟誓是军事首领们与战神签订的口头“协议”或不成文的相互监督“合同”。如果军事首领违约,战神可以惩罚他。反之,如果战神不保佑,军事首领也可诅咒它。其最终目的是借助战神的威力来激发战斗力。这是一种典型的求胜仪礼之具体表现。战神祭词就是一套富有感召力的语言符号系统。通过这些语言符号系统来为自己的暴力辩护,同时将敌方说成万恶之徒,使战争合理化是军事首领们的拿手好戏。正如赵鑫珊、李毅强合著《战争与男性荷尔蒙》一书中所说:“由于语言的产生,人类开始学会如何把自己非理性的冲动加以合理化,并通过双手学会制造武器。人类特有的攻击性也随之而生。这同后来文明期的战争找种种借口一样,语言在人类攻击性方面起着决定性影响。这一点,也是战争起源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只有通过语言作用,战争才打得起来。”正因为有了语言符号系统,人们发动战争或被动应战时,总是向战神或守护神祈祷,祈求神灵能够保护自己,并赐予自己战斗的勇气。萨满教战神祭词中的语言符号系统实际上就是为战争服务的宗教语言。
在北方民族中,萨满教的专管战争的天神后来逐渐被统治者所利用,将其发展成为政治意识形态之一的“天佑论”军事哲学思想。如成吉思汗统一了诸蒙古部落后说:“赖长生天之力,得天地之赞助,而匡普天下之百姓,俾入我一统之制矣。”他将自己的胜利归之于天神的佑护,而将敌人的失败也解释成“天不佑护”。帝王们巧妙利用这一意识形态来控制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企图以此来达到让国民无条件地服从的目的。萨满教在北方民族军事史乃至整个北方民族政治史上起到了综合精神凝聚体的作用。
在蒙古族历史上,萨满巫师和封建帝王间的合作也经历了从伙伴式合作演变为敌对式合作的嬗变过程。蒙古氏族从7世纪开始解体后,直到12世纪末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奴隶的战争。到了13世纪,成吉思汗终于将它们统一起来,并建立了代表封建贵族利益的蒙古大帝国。这些草原贵族起初遇到以萨满为代表的反对者,但很快萨满就意识到自己力量不足,于是看风使舵,改头换面,为统治阶级效劳。萨满教的巫师们竭力利用自己的职业骗取人民的钱财。
豁儿赤和阔阔出是两个有名的职业萨满。职业萨满往往被认为是神和人之间“互渗的媒介”。豁儿赤曾经为成吉思汗的登基制造舆论说:“俺乃圣祖孛瑞察儿掳来之妇所生者,俺与扎木合一腹而异胞者也。俺本不离扎木合者。然神来告余,使目睹之矣,草黄母牛来,绕扎木合而行,触其房车,触扎木合而折其一角,化为斜角者,向扎木合吼之,吼之,将土扬之,扬之,‘还我角来’云云。无角黄犍牛,高擎大房下桩,驾之,曳之,自帖木真后,依大车路吼之,吼之来也。此天地相商,令帖木真为国王之意,载国而来者也。神使我目睹而告焉。”很明显,这些职业萨满正是利用自己同胞们的那种可怕的无知,使他们的灾难、恐惧和愚昧变成自己的利益。他们把统治阶级神化,让人们相信统治者都是天上派来的,是天的意志的代表者,奉天承运,代天行罚的。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就是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会爱到无情惩罚。“长生天”概念的形成标志着这种天命观的确立。
蒙古萨满教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笔者认为,“长生天”概念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蒙古族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统一的神。笔者认为,“长生天”概念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蒙古族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君主,因而反映到宗教领域中就出现了一个统一的神;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能够从众多的个别事物中概括出一般的类概念。
这种天命观思想的形成,也是与统治阶级巧妙利用萨满教分不开的。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征金国阿拉坦汗时,“依俗登一山,解带至项后,敞襟跪祷曰:‘长生天有灵,阿勒坦汗挑起纷争,他无故辱杀我父弟兄斡勒巴尔黑和我曾祖弟兄俺巴孩罕,……我欲复仇讨还血债。天若许我,请以臂助,并命上天诸神及下界人类辅助我成功。’”这说明他对天祈祷,是想借助天的威力来争得“下界人类”的 拥护和帮助。同时,他也意识到要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必须争得那些在人民中最有名望、最有威信的巫师们的支持。因此,他给他们经济上的优惠和政治上的地位,如封豁儿赤“万户之官”,还赏赐了三十名美女。当蒙古大帝国建立后,成吉思汗把萨满教变成了官方宗教,重用“别乞”(意为大祭司),给予和诸王几乎相同的待遇,如被他任命的别乞兀孙骑白马,着白衣,“坐于上座而行祭祀”。从此萨满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教权开始介入政治。如,晃豁坛的蒙力克之子通天巫(帖卜腾格里)阔阔出,依仗自己的政治地位,无恶不做,为所欲为。他不仅殴打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儿,还经常在哈撒儿和成吉思汗之间挑拔离间,甚至还想聚众叛乱,争夺政权。成吉思汗得知消息后,即派其弟斡惕赤斤杀掉了阔阔出。
蒙古族萨满教是一种原生宗教形态。在蒙古族民间,认为宇宙万物、人世祸福都是由鬼神来主宰的。自然界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自在的体系,而是由某种超自然的东西在支配它,它是神灵的创造物,依神灵的主观意志而发展,变化的。自然的每个部分都是由某个特定的神灵所管理的。在蒙古族萨满教的天体崇拜中,天地和日月崇拜是较重要的内容。天地滋养着万物,日月温暖着世界。这种自然的伟大而神秘的力量往往被人们所神化,变成人们所信奉、崇拜的对象。首先被称为“万物之父”的天得到了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因为不管是对农业民族也好,或者对游牧狩猎民族也好,天是具有最巨大的生产意义的自然因素。在蒙古族生活的草原地带,一旦天下大雪或刮大风,牧民的牲畜会大量死去,帐房会被刮走。因此,天在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中成为诸神中之第一位神。蒙古人自古 “有拜天之礼”。据文献记载:“成吉思汗出征金国阿勒坦汗时,依俗登一高山,解带至项后,敞襟跪祷曰:‘长生之天有灵,阿勒坦汗挑起纷争,他无故辱杀我父弟兄斡勒巴尔合黑和我曾祖弟兄俺巴孩罕,……我欲复仇讨还血债。天若许我,请以臂助,并命上天诸神及下界人类辅我成功’”。蒙古语称天为腾格里,蒙古萨满教认为腾格里天神有九十九个,西方的五十五个天是善的天,东方的四十四个天是恶的天。这表明蒙古萨满教是从明显的功利目的出发去解释“天” 的,因而给它涂上了一层伦理的色彩,把它分成以善恶为代表的两个互相敌对的阵营。几乎在所有民族的萨满教观念中天神居首要的地位。
萨满教所理解的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失去了它的物质性,变成一种代表神灵的精神实体。作为物质体的同一个天在萨满教观念中分化成不同的天神,为了管理不同事物的需要天神内部也产生了不同的分工,其结果塑造出许多性格不同,千差万别的天神形象。
在蒙古族萨满教的观念中除了自然界的事物之外,一些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火等自然界的现象也被神化了。每种现象几乎都有各自的神灵。他们不仅把太阳、月亮等自然事物当作神灵来加以崇拜,而且还把火这一自然现象也当作神来崇拜了。火的使用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对于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人来说,火尤为重要。他们可以用火来驱赶猛兽、烤吃生肉、烧火取暖等等。正因为火对古代蒙古族的生活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因而他们特别敬奉它,甚至把它看作美的化身,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切祸根都可以用它消灭,一切污垢都可以用它净化。蒙古人的萨满教观念中,火具有清楚肉体和精神上一切恶习的本性。班札洛夫在《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一文中指出:“蒙古人虽然认为女神斡惕(意为火)是幸福和财富的赐予者,但它的特点是纯洁,它具有使一切东西纯洁的能力,它具有把自己的纯洁传给别的东西的能力”。古代蒙古人送到宫庭里的一切东西,事先都要通过两堆火净化以后才能送到可汗手里。火,几乎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灵。
蒙古人为了得到火的帮助,往往“把高山一样多的食物,把大海一样多的饮料,祭献给威严的火汗”。布里亚特蒙古萨满神歌中,火神的形象往往被描写成红脸老人或穿红衣的老人。对火的禁忌是萨满教火神信仰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如,古代蒙古族的萨满巫俗中,拿小刀插入火中,或甚至拿小刀以任何方式去接触火,或用小刀到大锅里取肉,或在火旁拿斧子砍东西,这些都认为是罪恶。据旅行家鲁布鲁克报道,他们相信如果做了上述事情,火就会被砍头,并且禁止从火上跨越。
打雷被认为是天在叫。《黑鞑事略》记载,古代蒙古人“每闻雷声,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杜尔伯特蒙古族认为龙生气后发出巨声,从而引起雷鸣。这一古老信仰在近代科尔沁萨满的祭雷活动中仍有残留。科尔沁有些地区,遇有雷击人畜或蒙古包,便请萨满来禳除。到了雷击处,萨满拿出蓝色旗供上,然后念咒祭旗,使那个地方“清洁起来”。当地人认为,一经萨满念经祭雷,就可免遭雷击。
蒙古族对神山和山神的崇拜古来有之。《蒙古秘史》载,三篾儿乞惕部落来侵击时,帖木真向不而罕山去躲避。三篾儿乞惕走后,成吉思汗对着不而罕合勒敦山感谢道:“于合勒敦不而罕上,遮护我如蚁之命矣。我惊惧极矣。将不而罕合勒敦山,每朝其祭之,每日其祷之,我子孙之子孙其宜省之。言讫,向日,挂其带于颈,悬其冠于腕,以乎椎鹰,对日九跪,洒奠而祷祝焉”[⑭]。这种爬上山顶祷告的信仰习俗在古代蒙古族中间流行较普遍。据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的《史集》记载,当花刺子模王杀死成吉思汗派去的商人时,成吉思汗得知后“愤怒地独自上山头,将腰带搭在勃子上,光着头将脸帖到地上”,祈祷三天三夜[⑮]。蒙古族自古以来把蒙古地方的孛格多山、查苏凸海日罕、杭爱山等山脉当作神山来崇拜并祭祀过。尤其不而罕合勒敦山是蒙古族祖祖辈辈祭奠下来的神山。
蒙古族萨满教中具有图腾崇拜的痕迹。据《蒙古秘史》记载,帖木真九岁时,其父也速该把阿秃儿领他去到舅家聘女。途中遇见翁吉刺部落的德薛禅。“德薛禅语曰:……我今夜得一梦,梦白海青握日、月二者飞来落我手上矣。我将此梦语人曰:日月乃仰望之者也。今此海青握来落我手上矣。正意白海青之落,主何祯祥?也速该亲家,我此梦,却主汝之携子而来乎!梦得好梦,所以有些梦者,盖汝乞牙惕百姓之神灵来告之也”。
蒙古族对树木的崇拜可能是基于对它的生命力的崇拜 。据拉施特《史集》记载,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颗孤树。他在树下下了马,在那里心情异常喜悦。他遂说道:“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就这样,成吉思死后,把他的灵柩埋葬在那里。这可能跟萨满教对活树之生命力的崇拜有关。另据旅行者普兰尼·加尔宾的记载:“窝阔台汗遗留下一片小树林,让它生长,为他的灵魂祝福,他命令说,任何人不得在那里砍伐树木”。这也同样表明,古代蒙古族崇拜活树的生命力,它往往成为死者灵魂栖息之处。蒙古族对活树的信仰具有很古老的传统。据《蒙古秘史》载:“全蒙古,泰亦赤兀惕聚会于斡难之豁儿豁纳黑川,立忽图剌为合罕焉。蒙古之庆典,则舞蹈筵宴之庆也,即举忽图剌为合罕,于豁儿豁纳黑川 ,绕篷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奚,没膝之尘矣”。那棵篷松茂树就是古代蒙古所崇拜的神树。
这种崇拜和供祭独棵树或“萨满树”的观念与中亚地区蒙古各部族认为自己祖先诞生于树木的神话观念有着密切联系。据《卫拉特史》记载,卡尔梅克蒙古人中的绰罗斯部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一个“以玲珑树做父亲,以猫头鹰做母亲的,柳树宝东(大力士)太师”。卡尔梅克蒙古史诗《那仁汗胡勃棍》中也把主人公说成是诞生于树木的人。在布里亚特蒙古神话中,有许多类似树木崇拜的描述,在布里亚特萨满唱词中还常常提到“柳树母亲”。
蒙古族信仰萨满教,相信人死之后灵魂不灭。成吉思汗去世于征服西夏的途中,遗体被运往故土埋葬。 成吉思汗生前留下秘不发丧的遗言,平定西夏后,在他生前的四大鄂尔多举行哀悼,每个鄂尔多举哀一天,由于有些部落距离遥远,后妃、诸王连续三个月从四面八方赶来祭奠哀悼。 成吉思汗生前四大鄂尔多 是四大妃子孛尔帖、忽兰、也遂、也遂干的宫殿。四大鄂尔多是成吉思汗生前居住和议定重大事项之地,分别处于四大妃子驻地,由护卫军把守和服役。成吉思汗去世后,护卫军继续服役于四大妃子,直至她们去世后,成吉思汗遗物、四妃子灵魂,随同鄂尔多一并成为成吉思汗祭奠的内容。成吉思汗去世后,按照蒙古族幼子继承父亲家业的习俗,拖雷继承了四大鄂尔多,根据成吉思汗遗言及属众愿望,拖雷发布了成吉思汗去世消息并组织后妃、诸王进行祭奠。拖雷是成吉思汗祭奠的发起人和最早管理者。古代蒙古人认为,成吉思汗居住过的鄂尔多和他所用过的遗物,吸收和依附着他的灵魂。因此,蒙古族灵魂观念基础上形成的鄂尔多祭祀,根本区别于中原汉地帝王陵墓祭奠。
此后,蒙古族历代统治者都继承成吉思汗的衣钵,对萨满教采取有时扶持有时镇压、有时利用有时排斥的态度,使萨满教一阵衰落,一阵恢复。直到16世纪末叶,萨满教在蒙古族统治者的绝对禁止、一律消灭的果断措施下遭到了“恶运”。俺答引入佛教几十年后蒙古汗权结束,蒙古各部先后归附了清朝。为了统治顺利,藏传佛教成为清朝怀柔政策的组成部分。清朝鼓励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到蒙古地区传播宗教,大建寺庙,消弱蒙古的战斗力。清朝统治期间,蒙古地区喇嘛遍地,寺庙泛滥,佛教景观随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族萨满教进入了衰落阶段。
[英]道森编《出使蒙古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