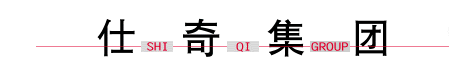用户登陆 用户登陆
|
|
|
|
 项目列表 项目列表 |
|
|
|
 项目搜索 项目搜索 |
|
|
|
|
|
 项 目 展 示 项 目 展 示 |
|
| 您现在的位置 >> 所有项目 >> 百家论坛 >> 中国第二届草原文化百家论坛 >> 特邀嘉宾 >> 席慕蓉(著名女诗人、散文家、画家) |
 |
| |
|
项目编号: |
3251649216 |
项目名称: |
席慕蓉(著名女诗人、散文家、画家) |
项目备注: |
|
| |
|
 项 目 说 明
项 目 说 明 |
我心深处
席慕蓉(著名女诗人、散文家、画家)
各位好!
一开始讲蒙古,我就停不下来,常常是霸占了整个讲台,然后不让听众离开,这是我常常容易犯的错误。所以今天先把表拿出来,好提醒自己。
非常感谢给了我两个半钟头的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要问,那剩下的时间就留给各位。
首先要谢谢邀请我来的各位朋友,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回到自己远乡的土地跟自己的同胞可以有更长时间的交谈。另外我也要谢谢今天到来的各位,大家在这么热的天气愿意走这么长的路过来,我想一个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家喜欢我,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可能是大家喜欢这个蒙古高原,所以我定的这个题目 — 《我心深处》。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前面换过几个,可是我总觉得我自己回到了老家,我应该用自身的经历来跟各位对话。
我们一般人所受的家庭教育,通常是不会在别人面前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如果这个“我”频繁地出现的话,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奇怪。如果我自己退一步给我一个比较大的距离,我说的这个“我”,是一个在整个大的时代里的一个小小个体的经历,也许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上个月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去,他们要给我出版一本书,我想大家也许看过,他们出过一套书,是沈从文和他的《江西》。还有一本就是马上就要出版的王蒙和他笔下的《新疆》,计划中的是张爱玲和她的《上海》。他们希望我有一本是席慕容和她的《蒙古高原》。
对我来讲,这件事情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参加这么一个丛书的出版。他们是以图片为主,文字比较少一点,是以一本有四、五百张图片的那么一个大开本的书。我把稿子送过去以后,跟美术编辑、文字编辑开始坐下来讨论这本书怎么样出来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是要出一本介绍蒙古高原的书呢,还是要出一本一个从小离散在组群之外的蒙古人怎么去寻找他原乡的的这么一本书?他们说当然是后者了,所以我们就得先把这个序文写出来,底下的东西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我就带来好几首诗,我本来是想用那首诵歌 一 就是关于蒙古帝国辉煌历史的那首诵歌来当作序诗。可是总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就后继无力了,我前面把蒙古帝国的这样一个我对它的歌诵放在前面,后面我就没有东西支持我了,因为我知道的太少。我一眼看到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旁听生》,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它背下来,我试试看:
没有山河的记忆等于没有记忆;
没有记忆的山河等于没有山河;
还是山河间的记忆才是记忆;
记忆里的山河才是山河。
我可是两者皆悟了,是的,父亲的故乡这座课堂里我既没有学籍,也没有课本,只能是个迟来了的旁听生,只能在边远的位置上静静张望,观看一丛飞燕草如何擢升旷野;一群奔驰过的野马,如何在我突然涌出的热泪里影影绰绰地融入那席暮间的霞光……等我把我个序诗决定下来时,好像觉得对了,另外两位也都觉得这个序诗恰恰就是对我自己或者对这本书的一个开场白。
我今天早上听了好几位专家、学者的对草原文化的解释,还有对它的期望,对它很多所谓一种更深层的诠释。对我来讲,我这个旁听生从1989年到现在16年了,虽然是迟到的,可是现在年年都来每次对我来讲都是又学会了一点,又多添了一点课程,又能够得到一些宝贵的知识。
现在我跟各位要讲的一件事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那个时候,是1989年或1992年左右时间,我已经开始回家了,而那个时候的家,是我的父母给我的乡愁。可能我想在坐的各位,也许都是我的读者,也许不是。(你看我又来了,我总是跑野马又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了)我现在跟各位解释一下,我的父亲的蒙古人,我的母亲也是蒙古人,从小我是跟着外婆在家里长大的。父母对我的教诲跟外婆对我的耳听面壁, 一直让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个蒙古人,而且很以自己的血源而自豪。但是我的教育系统里蒙古的知识几乎为零,或只能说比零多一点点。所以我一直就是说自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蒙古人。能够回到老家,觉得自己求知欲很旺盛。大概过了两、三年,觉得自己的乡愁、自己的疑问能够逐渐地可以就回到了蒙古高原,去得到很多解答。
台湾五月左右就开始有台风,那年6月底,台风刚要来了,傍晚我就走到我家的山坡上面散步,天上的云霞是很恐怖的,绿的、红的对比色,上边是黑的,闷闷的压首,风已经要来了,相思树、竹森已经开始觉得受到威胁,我自己走在山坡上,忽然间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熟悉的感觉,重新回来的一种欢迎的感觉。
假如我自己是在台湾旅行的人,不在台湾生长的人,他现在站在山坡上他会吓死,面对这么一个恐怖的天空,层云堆积,红色、绿色的霞光。你觉得大自然的颜色变成了红的,一种好像科幻片的样子的感觉。可是以对我呢,我是觉得我在台湾这个岛上已经活了50年了,我的身体、我的发肤、我的毛孔、我的心里的感觉,哈哈!明天要来台风了,来台风之前的低气压对我而言是很熟悉的,隔了一年了它才又开始刮台风的时候好像老朋友再见面的那种很熟悉的感觉。虽然知道是台风要来,可心里面还是有点觉得蛮亲切,我忽然间觉得很得意。我的意思是,台湾可以真的说是我的本土了,真得是我的家乡了,我从整个身体都在接受它,很奇怪,我正在暗自得意的时候,忽然之间心里面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甚至我分不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那声音说:“难道就这样,难道就在这个岛上过一辈子吗?”然后等我一楞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没了。我一个人站在山坡上,在那个时候,我忽然发现原来在我的身体里面还住着一个另外的我。而那个另外的我平常也没有现,可是就在那个在我所谓我自己以为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完全的一个状态里面正在有反映的时候,有一个更强烈的我发生了。那个时刻,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经验,后来我把它写过一篇短短的文字。
今天早晨有好几位学者问我,我们是谁?我们从那里来? 我先问他是谁?对他来讲他希望生活的地方在哪里,这其实也是我今天为什么作这个题目的原因。
“我心深处”好像有点文艺腔,可是我心深处还有一个我,我想我现在十几年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寻找那一个“我”,他要什么?那个我的所谓的他的记忆的什么?是什么能够让他觉得亲切、让他觉得心安?也有人觉得我很奇怪,奇怪你回家吗?一次两次也就够了,你没事老回来干吗?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解释。我跟各位说,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总认为我们眼见的我们才信,我们没有看到的我们不信,我现在自己确实是亲身经历了这亲心里面一人呼唤,对我来讲,我相信。所以我有时候回来十几年以后,我常常觉得我很希望能够台湾这个居住了五十年的岛屿不是我的家乡,可能是我从1989年以后,我又发现了我的原乡。原乡在前几年的时候我觉得它是我的乡愁,到后几年,尤其是最近十年,我觉得这是整个游牧文化对我的一个强烈的吸引。我觉得我是来到一个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是在我住的五十年的岛屿上面的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不了解的,所以我常常会带我拍的幻灯片去演讲,演讲的时候一个钟头一定不够、两个钟头也不够,每次都是急得要死,急得想跟别人解释。非常急的原因就是觉得很奇怪,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如果我现在跟别人说莎士比亚,马上那个背景就在了,如果我说哪一个人的角色,别人就了解。问题在于当我说蒙古的时候,包括我出新书,每一次新书的新闻发表会里面,年轻的记者来问我内蒙古在哪里?蒙古国在哪里?你说的克尔马克在哪里?什么叫阿尔台共和国?什么土呀?统统不知道。所以我要在我的新书发表的时候开始先上历史课、地理课。
其实我的历史课、地理课也是补来的,我去演讲的时候就着急很多背景都不够,后来我发现了,我真正的着急是什么呢?是因为我要扭转,我想要把我们在汉文里的教育融合农耕文化的教育里面,我现在举台湾的例子,在台湾教育体系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已经很固定的形成。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百年,大家都在谈论爱因斯坦的时候,有一些报道里面就提到一些科学家认为在我们生活的宇宙(如果我们称呼他为正宇宙的话在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还无法测到的空间里叫做反宇宙)。或者是人或者是事都是跟我们相对应的,但是好像很多东西也可能跟我们是相反的,那是一个反宇宙学家说,但是在那个反宇宙上面生活的如果是人类的话他们的科学家和他们解释:在我们的宇宙之外有一个空间里面的生活着跟我们相反,跟我们两两对应的世界我们称呼他为反宇宙,科学家现在还找不到这个反宇宙的存在。
怎么证明他的存在呢,比如我们有很多粒子,有粒子的话就有反粒子,当这个粒子跟它的反粒子遇见的话是会互相碰撞,所有的质量就消灭了,转换成能量,很容易举出的例子就是我带有负电的电子,当它和它的反粒子就是正电子相遇的时候互相碰撞,一切的质量消失,转换成为光,我觉得很迷人, 常常觉得科学里面的东西很迷人,我认得科学界的朋友对我说,如果你要解释的话不要说是我教你的,因为你一定会说错,说错了的话,他们会负连带责任,但是现在我现在想到了,我在面对我的听众的时候,我的听众是从一人农耕社会教育的文化出来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正宇宙,当我们在游牧文化里面,他们会认为不可思议的相反的,因此,我们在演讲的时候会特别辛苦,所以现在我知道了我只要举出两个例子,那么也许我们在观念和观念之间碰撞的时候,碰撞是一个消极的感觉,但是我现在感觉相反,当我们在观念上的不同,互相碰撞的时候,我们的偏见会消失,所谓能量就转化为我们互相沟通的能量,就我现在去演讲的时候我都会和他说两个很明显的观念,因为我有一次读到一位我们台湾作者写的我们二十一世纪的都市里面,常常是有两种这个情况很矛盾,一个是安稳定居的,要不要选择安稳定居,他括弧里就写(有家的感觉),还是选择游牧迁徙(无家的观念),他说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在城市里面处在这两个矛盾的状态。我觉得这篇文章太好了,他刚好拿来让我和听众解释,原来在农耕社会里面认为只有安稳定居才叫做有家,那游牧社会里面的游牧和迁徙铁定是无家,当然我一定解释这位作者并没有与我过不去的地方,他只是用整个社会里习建的观念来解释他要说的东西,我就问,请误问谁能说我们游牧民族是没有家的人,我说我们有这个字比你们还直接呢,你们把住的房子叫居室,或者是住宅我们就把我们住的毡房、毡帐、穹庐,我们说家,这个家唯一和你不同的,我先说和你相同的好了,这个家我们也是在里面防寒,避热,我们在里面可以修饰、可以美化,我们可以用这个家来向别人夸耀 们的品位,我们的财富,这跟你有个家不是一样吗?还有全世界的人对家的观念就是,这是整个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他的悲欢记忆累计的场所,所以是我们每个人童年的美好的回忆,也是每一个游子出门的时候心里面的一种依恋和向往,你说这个家跟你的家有什么不一样,除了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移动而已。
在农耕社会里面从来没有人会说,游牧不等同与流浪,对他们来说,游牧等同与流浪,所以这就是一个正和反对家的感觉。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听众知道这个很明显的我们所犯的一个错误;第二个对土地的看待,我是用一个汉文里的荒这个字向听众解释的,其实那是我在乌珠牧沁的草原上面,我去一位牧马人的家里布赫鄂尔登先生的家里住了一个晚上,后来又在那样广阔的草原上走了好几天。有一天晚上,有一点月亮,走在小林子的旁边,我忽然觉得我在我所修习的汉文的文字里面找不到一个字来形容这样的感觉。汉文的文字,是没有办法来形容蒙古高原的很多情景的,如果说看到这一大片我们会说荒野,或者我们在汉文里面这个“荒”字会说荒废、荒制,这都是含有一个谴责的意思,所以我们常会说这有一片荒地,这个主人太懒了,没有想到把这块地耕一下让它变成良田,所以土地的价值在乎他有没有被耕种,能不长出庄稼来。
我自己是很遗憾的,五岁以后就没有学习蒙文的机会,所以对我来讲我只好问我的朋友,问在我们蒙文里面怎么形容那种荒野、或者旷野我们怎么形容,他说,我们说那是无人之地,就是亘古以来,我们人类的脚没有踩上过的地方,我们形容长满了青草的大地,我们叫它为有皮之地,因为我们认为土地是母亲,就像是身体上的肌肤一样长满了青草,如果被大量开垦了的土地,我们叫无皮之地,就是濒临死亡的大地。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在汉文里面,“荒”就是一件坏事,是被谴责的一个行为。所以大家热衷于开荒,开荒是被鼓励的行为,但是问题是你在哪里开荒,什么叫做荒?你为什么认为它是荒?而我们认为它是生命的海洋。这个问题里面就是两种文化正与反的矛盾,我不能说谁对谁错,我只能说所有的这些造成我们现在草原沙漠化的原因之一,其实也是因为农耕文化里面的所谓颠扑不破的真理: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栽。深耕勤耘在整个的亚洲东南部来讲,是绝对没有错的,可是如果在亚洲的西北部就是很大的错误了。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土层的厚薄。
我到新疆巴音布鲁格草原上的时候,朋友跟我说,地底下一公尺一公尺半为涌动层,我想蒙古高原上可能一公尺下一下面就是沙。前两年一位呼伦贝尔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如果我们有一公尺的土地,我们就不担心草原沙化了,我们的土地其实只有薄薄的几公分,所以我有一个学佛的朋友他说佛陀走路的时候脚步很轻,因为他认为土地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他的脚步踩上去如果太重的话土地会疼痛,佛陀心里觉得舍不得。那我就想说,假如佛陀行走在蒙古高原之上的话,我想他的脚步要走得更轻,因为我们那薄薄的几公分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会疼惜的,希望土地能够永远保持生命力,希望佛陀在上面大发慈悲,然后会在心里更加心疼、走的脚步会更轻。
我带幻灯片来了,我们场地很大,所以幻灯看起来小一些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作为参考好了。我差不多有两万张的幻灯片的图存,我每年一回来我就把我认为是好的先分出来,其实两万张里面有一万八千张是不好的,可是我也舍不得丢,就把他放在旁边,后来有一位朋友,他告诉我说上海文艺出版社书的时候,你其实也应该去你认为不好的照片里去找,因为你所认为好的东西都是规规矩矩的,你认为不好的照片里面其实可以找出非常好的照片,结果我去在一万多张照片中找出一些很多我当年认为不好的,但是也很辛苦,刚好找到几张我大概是1985年的照片(放幻灯片),很像一个江南女子。
我们再看下面一张(放幻灯片),我给大家看1989年,还没有回家,快回家了,请大家看1989年8月底回到了家的席慕容。请看,怎么一下子就从一个江南人、台湾人变成了一个蒙古人了?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放幻灯片),这是1990年在我父亲的草原上带着我的两个侄孙女在走。好我们在往下(放幻灯片),这是蒙古国的宝格塔山的下面,然后我们再往下,这是我回母亲家乡2003年我穿上我们蒙古的衣服,我自己觉得很美,因为没有办法放羊,只好假装和一只小羊走一走。那么这张请各位看(放幻灯片),这是我去年在白城查干浩特,我们林单汉的都城跟蒙古朋友拍的,会不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当地的蒙古人了,我觉得就是了。现在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土地慢慢对我有影响,那到你的年龄对你没有影响吗?但是我要说在台湾变老的和在蒙古高原变老了那是有差别的。在蒙古高原上的行走其实就是一个旁听生。
(放幻灯片)这是我们鄂尔多斯成陵旁边的敖包,我慢慢的一点一滴给大家看,大家想问那三棵树的意义,那么我今天想问在座的有几位学者,为什么在成陵的敖包旁边种三棵树?我很想要来请问。
(放幻灯片)这是元上都的敖包,我去年去正蓝旗的敖包。(放幻灯片)这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敖包,这个是锡盟我去乌珠穆沁路上的敖包。(放幻灯片)这也是在锡林的敖包,(放幻灯片)这个是在阿拉善的额吉纳旗。我实在觉得很伤心,在地图上还是一个浅兰色的湖泊,可是在实际的两千年生命里面已经干涸八年。(放幻灯片)这是居延海旁边的包勒敖包。额吉纳旗的朋友在上海读大学,他们一放假老师就带他们去居延海去游泳,好的湖,旁边长满芦苇,可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干了八年,而他干了八年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甘肃省,这个黑河上游的居民切断了水源,不供应水源40年,前几十年不好意思还偶尔给一点,但大片的枯死的时候,在文字上说因为牧民的原因而枯死,可是明明是因为上游的人把河流切断,我想不通,如果我们是两个是敌国的话,你把河流切断,那也许说是战争的原因,如果是和平的话,同样一个国家上面怎么会有人把河流切断呢,所以我认为像这样子干涸的了居延海的旁边我的朋友还在向敖包、祈求,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好像在我们旁边,可是我没有办法形容他是什么,正好有位学者也是这么说的,在我心里我有一点小小的得意,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用我自己笨脑袋去想的,我又没读过书,为什么我今天早晨他们说整个这个文化的氛围是无声的,而有一位朋友将到对的演讲标题是宁静的巨大,高原就是这个,宁静的巨大不只是地的广阔,还包括文化的氛围,可他是无言的,我们很多文化是无言的,把这个无言的东西变成具象的文化特色,怎么原来我想的也有一点是这样,刚才那个敖包是我父亲家族的,我到现在还是想要继续的去问,敖包本身是当时你有一个大区域的纪念的敖包,可是一个家族真正要代表的是什么,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父亲的天空锡林郭勒盟,我们看下面的一张,这是我母亲的家乡克什克腾,因为土地都没有了,当然你是说住在上面的还是自己的亲人,但是从前的那种都没有了,但天空还有吧,我就拍天空,是在我去阿拉善经过沙漠的北部的日出,下面几张我是觉得这就是所谓地域性介绍,这也是文化氛围,我们是这么活着的,在这样的区域,这么广大,他吸是草原圆周的十二分之这或者十八分之一,我们如果在草原上我们会永远觉得我们就是草原圆心的一点无论你走多少路,圆圆总是围着你,那种感觉是跟你在都市里经过十字路口的差别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很有名的草原的骗局就在这里,怎么叫草原的骗局呢,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说走到草原上,请问往哪个地方去,有多远,遇到一位牧马人就告诉你说就在那呢,大概下午就到了,他说就在哪呢,就在那呢,也许两个钟头就到了。我去哈林浩林,去拍那个故都的遗址的寺庙,天气很好,我的旅馆远远的看得见,我们不好意思让司机等我们就让司机先回家吧,他就问:你走的回去吗?我心想,拜托这么点路,怎么走不回去。结果我走不回去,走的腿都断了,那个美丽的旅馆还是在我前面,结果走了好几个钟头才走回去,结果倒头就睡。这是我们最有名的草原的骗局,因为中间的阻隔的东西方没有象我们在城市里面那么清楚,这里面就有一个对时间的空间的无限大,也让我们感觉到时间上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巴尔虎草原,我到了上面懂得汉文里面的“地老天荒”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亘古以来它就在那里,在这上面发生了很多很多事,都是真的,我都相信。
这是去年夏天在乌兰布通,这个水草丰美后面有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葛尔丹在这里被康熙打败了,听说这里战场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所以当地的朋友说晚上会听到哭声,也许别人会说你说的是怪事,但我不觉得,就象马可波罗在游记里说:“在额吉纳的沙漠里面会有声音在”,也有朋友解释说,很可能是过往的朋友的声音在这里留下来,遇见什么情况就出来了,当这么多生命在这里被突然的消亡的时候,我感觉也许会有晚上在这么水草直美的地方听到哭声。
(放幻灯片)这是沼泽。这是在巴尔虎草原附近的沼泽,我今天还没有带很多关于有水的照片,我平常在台湾演讲就会带很多瀑布、湖、水的照片,我最不喜欢别人一说就是大漠、就是草原,蒙古高原上的地貌是有很多的,地貌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人一讲就是大漠,我最受不了这个,这有很多水呀。这是小加丝台正蓝旗元上都的后面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日落。其实如果你说这样, 一般的人真的对蒙古高原的陌生,大家只能怪我们的教育制度。
(放幻灯片)这个就是说大兴安岭的噶先洞,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先辈逝世,我后来访问到了米文平先生,一千五百年历史书上的谜题给米文平先生在1980年找到的。他找到的也不是突然的想到的,但是问题是,并不能够证明它是事实,除非你找到刻在上面的字,他去了四次,到了第四次时候刚好是下午四点钟,下午四点钟的太阳是斜的,照进洞里面,如果我们面对这个洞口,它在洞口这面的地方就有有些凹凸的阴影,然后米先生眼尖看到一个“四”字,他就说有字吗,然后拔苔鲜,然后每一个人都开始拨苔鲜,然后每个个人就疯狂的说有字有字,然后拨了一下,“太平真君四年”,找到了,这就是那个伪书上面留下的一千五百年的谜题,给这个米先生发现了,后来我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们都疯了,一直拨一直,等到想到要拍照的时候,他说已经到四点半了,他说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都是忘我的,是疯了的,我想假如有一个考古学者能够在努力了很多次以后,揭开150年的谜题的话,我想不疯也难。所以我很同情他,不过他现在没疯,他现在继续在做鲜卑史的研究,很可爱的老先生,我非常敬佩他,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好几位考古学者曾经在1960年的时候去过阿里河都到那边去了,都到了阿里河,当地人说请你一来,这里有噶先洞,你们要不要参观一下,听说那几位老先生说还是去跳舞吧,结果没有上山,又让等了二十年。这是大兴安岭都去了好几次,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我刚去了,鄂温克的朋友说,欢迎你五年再来吧,意思是说我很远吗,不能年年来,因为我很远吗,不可能每年都来,结果我每年都来了,所以每次都说不好意思我又来了。对我来讲,我从来不知道,桦木的文化是在大兴安岭来的,从芬兰一直到大兴安岭一直是属于桦木文化,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都以为只在俄国的文化里面,在日本的屏风上面看到桦树,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我的原乡,原来也是桦树的原乡。
(放幻灯片)这是落叶松在雨后彩虹的下面,天是全黄,可能糨子松是全绿,白桦树是灰的,如果大家第一次去大兴安岭一定等第一次下了霜的时候去,没有比那个时候的大兴安岭更美的地方了。我们再往下,这是她的早上,各位可以看的到,大兴安岭的叫做“巨树的故乡”,当地的朋友不是只有蒙古人和我们说,当地的汉人朋友也跟我说,从前要是进去的三棵树要砍掉一棵树才能进去的。 现在已经四、五十岁的行政人员他们在读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最喜欢做的事是拍前面朋友的肩膀一下,然后躲到旁边的树后,那个朋友就找不到他了,现在你到那去拍一下,四野一棵树也没有,你拍完别人一看就是你。所以有时候我要说对一个土地的心疼不一定因为你是哪个民族,你看到你的童年曾经有过的美好的土地一点一点的消失,那种疼痛我我想任何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
(放幻灯片)这是大兴安岭上的急流河,我多拿了几张,因为我喜欢给别人看水,急流河是我们的祖先,这里我要问,在大兴安岭上面,还是这个急流河,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几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跟我看到的是同一条河流那种感觉,生命里面的些东西跟你相呼应,所以我会特别带来这么多张过来,这是一个草原录,上面有半个月亮,这是在蒙古国的一个岩画。这是红山、赤峰,我母亲的家乡,红山在蒙文里是乌兰哈达、也是赤峰,其实我喜欢家乡原来的名字昭乌达盟,昭乌达盟感觉到很有诗意,我们每一个人的遗憾,就是家乡的名字老是改来改去的,找不到一个古老的名字,一个古老的名字其实当地的文化的累积的中心,如果有一个古老的名字留下来,你会觉得很安慰。这个红山说得就是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周边,这个地方刚好在赤峰市里面,我的朋友带我上去的,这个附近的最早的是日本的考古学者在这个周边发现的新时器的很多痕迹,最近我们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也是越来越认真。我的感觉是有很多东西,我虽然不会解释,但是我总会觉得很清静。这就是红山的祭坛,当地的考古学者朱达先生刚好它是在辽宁省的凌源,在这个周围,在这凌源这个地方,跟我们刚才看到赤峰不一样,赤峰的附近有生活的痕迹,而在这个地方,全部是墓葬、或是祭祀遗迹,我从旁边拍的,我想大家一定会看到,从空中拍的时候一定会是一个圆型的祭坛,旁边三条首期的边线是用石头五千五百年黄山文化鼎盛时期,用手把石头彻的好像是长方的砖的形状,一块一块插到土地里面,当我看到五千五百年它没有消失它没有改变,我的腿都软了,虽然我现在给各位看到东西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显示,但是那里面有一些东西,后来我就去问朱达馆长。这么多年来,也就是今天早上的会议的里面我也想到的这个问题,在这几千年来,有这么多的灾劫,也有这么多不同的事情会发生,可是这个游牧文化始终没有消失,我们所知道的如果是更早的是也许我们找不到更确切的聚积,那么当我面对这样一个五千五百年以前的鲜明的对宇宙中心的祈求的祭坛的时候,我心里的感觉是其实它并没有真正的消失,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释这个意义,但是它是有意义的,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消失的。
我们再往下,这是我在蒙古国的不路根省的叫做鹿史,是为了英雄的纪念还是突厥文化里面,这个我完全不懂,这个就是我这次要来问几位朋友的,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拍下来,我把它带来,你看它刻的非常现代,我认为这个文化早年时候,这么早的时代里面,它的线条它的想法非常现代。我们再往下看这也是另外一个鹿史,浮雕的感觉,他的纹路其实是一种兽类的。
(放幻灯片)现在我要给大家讲,这是我刚回父亲的草原上的时候,我是一个伤心的蒙古人,这就是我父亲的家,这个家听说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家、很有规模的家、有很多毡房、也有固定的房子的家族,我回来时候只剩下了这个。我到鄂尔多斯听说在四十年前有静鹿在行走,一个人告老还乡的地方鄂尔多斯,可是四十年前的鄂尔多斯到处是很茂盛的红柳,你钻都钻不进去,有很多雀鸟,可是我去的时候是这样的鄂尔多斯。往下去,我不知道用铁栏杆围起来做什么,对,请您回头看一下那棵树,这样一棵树很奇怪,我自己时常看过,但是在鄂尔多斯的时候我是个伤心的蒙古人。但是常常会在路上,我们会遇到蒙古人很好客,民里所发出来的善意,在路上遇到不相识的人也可心下来讲话,可以好好的说一下你从哪里来,前两年吉林电视台有一个回家的栏目,刚好我在上海有个新书的发表会,他让我在上海的黄浦江前面说,说我的蒙古高原,我就说你把我领到这来让我怎么讲我的蒙古高原?我当时说请你们看一下,我面对的电视机请你们看一下我后面的千门万户的上海,如果你是一个陌生人的话,没有一扇门会为你打开,但是在我们蒙古草原上,没有一扇门会对你关上,即使你是一个陌生人。
我要向上海人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歧视,假如我住在上海,我也不开门,这是一个城市生活里面,生活的环境让彼此猜疑,假如我住在草原上有人来了,请进,我们会尽自己的祖训,其实成吉思汗的祖训是在善待行旅,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心里面自然发生的,在草原上总会遇到。我忽然觉得好像是草原上的,草原在消失,但是我们的人还在,我们的人对世界的态度没变。
这是在布里亚特的首都乌兰乌德,为蒙古同胞。 这是布里亚特,真的很帅,这是不好的幻灯片里面找出来的,好像谁也不清楚,没有拍到正面,后来发现我还是在感谢下面的朋友,感谢他对我的指教。我想要讲我是生活在这么广大无边的土地上,所以我们的心里边,自然而然的对时间逐渐的消失感慨很深的,可能这就是所谓草原的骗局吧,草原没有 一个阻隔,不像城市告诉你这是一路、这是二路等,可是草原上会觉得地老天荒的感觉其实是那首歌让我们颓废,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假如我的先生和我的女儿在底下座的话,他们一定受不了,从小我母亲就说我是一个半疯,这一回到家就全疯了。天上有风不系缰绳,地上的风我们难以永存,但这就是我们蒙古民族在这么一个广大的世界里生活的心里感觉。我知道世界是这样的,所以我好好的珍惜我眼前的每时每刻,你怎么能说那不是颓废呢,我觉得总不要说是万寿无疆吧,不要说谎吧,世界上怎么可能万寿无疆呢,我们承认我们生命的短处,可在这样大环境里,我们的生命的珍贵,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我知道好像在哪个里面,在每人仪式里面细节是文化的有一个纯粹性。
我在向大家报告我是鄂尔多斯的荣誉公民,非常得意在父亲、母亲的家乡的话我是天然的那个地方的人,但是鄂尔多斯的人给了我一个肯定,现在人说现在文明会影响我们的文化,我到觉得不是,朋友起码走的时候不会觉得离情奕奕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还有手机呀。
这是小孩子大概要跳萨满的舞蹈,整个蒙古高原上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个文化在逐渐的消失,但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停留,在停留的是间当然有创新、也的传统,我是觉得说我现在 比他们还要乐观,这是我们自己的因为生活上的空旷的原野里面我们养成的一种审美观,灿烂的、饱满的东西,这是我心里的渴望,所以在这里我只是因该把这个审美观多说一下。
这是藏传佛教的,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比较孤独。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分散,所以为了生存的需求,我们的渴望丰富的多彩、饱满的装饰。这里在乌审旗文革的时候破坏的的很厉害。听说文革的时候把放在沙漠里自生自灭的人,因为有佛祖的保护他们还是回来了。
看下面的一张,这是在广中寺,就是六世达赖喇嘛圆寂的那个寺,在阿拉善盟广中寺赖喇嘛里,听说文革时候光中寺准备要盖一个新庙,我觉得我要谢谢我回到蒙古高原后身边的每一位朋友给我的指导,给我的牵引,给我的提醒,给我的触动。那天要看广中寺修建的工程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很沮丧,我的意思是说庙已经毁了,你重盖有什么用?我旁边有一位人类考古学系的女孩子跟我一起去的,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席老师你看历史上那一座庙宇不是毁掉再重盖的,毁掉再重修的意义,你不能说它是消失了,只能说它是努力的延续。我一听,跟我女儿一样的年龄的一个女孩子把我教训了一顿,我忽然懂了:怕什么?毁了再来,再来本身就是这个信仰真正的地方。
(放幻灯片)这是我们的哈扎布,我们的蒙古的歌王,我1996年的时候跟着拉苏荣先生去拜访他的,我写过关于哈扎布先生生平的故事,他有一本蒙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哈扎布先生的一生一世是不得了的,有丰富也的坎坷,1996年,老先生已经有一点中风了,我们大家对他说要注意身体了,他说我现在感觉就好像装上了银鞍子的马,还像一个有着秘密恋人的喇嘛,我兴高采烈地往前走。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就是一首诗,更多的面对生命的态度。
哈扎布、拉苏荣是艺术上的神树。在台北乌日娜的唱片很畅销,她到台北去唱,前面有一些歌者唱完了,大家反应很有礼貌,乌日娜唱长调,唱完了之后,大家好快乐的鼓掌,然后希望她再唱,就是不放她走。结果主持人讲如果你们让乌日娜在唱一次是可以,但是非常抱歉的是我们不能用钢琴伴奏了,蒙古长调要用钢琴伴奏很奇怪的,可是我们用钢琴伴奏也能感受到,再唱一首完全没有伴奏的,一首歌下来我会觉得我自己进去了,全场的人都进到里面了,没人听的懂歌词,但是没有听不懂歌词,音乐在那里忽然会让我们觉得往上走,到了一个我们灵魂从前从没有达到的地方,把我们带到那儿去,深呼吸,然后在把我们带回来,在那天晚上,我感觉这个艺术是无法替代的,它是我们文化上的神树。
我不反对把很多蒙古歌曲翻唱给汉文的朋友来听,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和我说,蒙文的歌翻汉文就不好听,因为歌是跟着原文的词义走的,请问有把意大利的歌剧翻中文唱的吗?我们能把它翻成汉文,但只是把它当介绍,艺术本身在这个时候是不可翻译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曾听到一个唱片,是把妹妹我想你呀、一个紫丁香呀,然后翻唱长调的唱法,我的心很痛,民族和民族之间需要沟通,但沟通不是把我们民族文化的纯粹性放弃了,那不叫沟通,那叫投靠文化,投靠另外一个文化的时候,文化就消亡了,我为什么喜欢一个文化,为什么爱听蒙古长调,就是因为你可以用你的声音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我现在的感觉是,很多人常常在说用蒙文唱长调的人,说他是固执的、保守的,或者说他没有迎合时代,但是时代是随时在变的,艺术是不变的,真正的艺术,不是所说见山是山,然后另外一个年龄,我们又是见山是山。长调就是那个山,不要给它改来改去的。
很高兴长调在申请做世界文化遗产的申请,坚持用原文来唱蒙古长调的歌者他绝对不是停止不前的,相反有很宏伟的前景,可以看得很远。不唱的话,有一天我们会很想念,有一天我们会后悔都来不及。
(放幻灯片)这两位是在神树的旁边的牧民,他们后面这两棵树,300岁了,这两位夫妻就是在这个神树旁边的小树苗刚出生的时候用各种方法保护它二十年,又有一棵小树长大了,没有人要求它,没有人给他薪水,没有人给他奖状,可是自然而然他们会让这样的生命让他继续长大。我看到很多细节还在我们孩子的身上。
(放幻灯片)这张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也是我去鄂尔多斯,那个城市里的一个母亲让他的孩子给我们唱祝酒歌,给我们唱完祝酒歌以后,这个孩子给我们敬礼,你看他的手的那个角度,只有蒙古人用这个文化的细节。我们如果到了法国,可能这样可能那样,或者我们现在怎样的敬礼,你看那个蒙古小孩子的手的摆法,那个细节是靠什么,靠母亲、靠父亲一点一点给他的,好象在鄂尔多斯现在还能看到,信仰还在,所有生活上的细节还在。我慢慢的变成了一点都不绝望的人。
(放幻灯片)这是在这个大兴安岭,应该是根河,还是鄂尔古那河旁边,有一个这样的水,他们说是我们圣祖成吉思汗马蹄踩的印子,像个马蹄,所以神话也在,都在有智慧,这两位都可以说是长胜将军,穿着他们有彩带的衣服。(放幻灯片)这就是布赫尔顿先生的家,他的小儿子上小学四年级,回来时他的父亲还是希望他能够放羊,你可以说他是固执。乌珠牧沁的草原有很多东西都在改变,可是还是坚持去学习在社会上所必备的技能,但是我还是希望回来能够继续我的父亲的我的祖父所让我做的这些牧马的事情,我在问布先生的时候,我说你什么时候有幸福的感觉,你的幸福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说我看到我的牲畜能够平安的生长,看到它们在这个草地上没有任何灾害的时候我的心里觉得很幸福。其实周围的大环境已经改变了。
我有一位朋友童年时候家里遇到了困境,所以母亲把马鞍拿出去卖了,所以他的童年一直有个遗憾。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亲手为他打造了一个亲马鞍,他说把这个马鞍放在城市的自己的公寓房子里面一进门的地方。他没有马,只有车,他还是把这个马鞍放在屋子里面。我们会认为有意义吗?可是生命其实就是这样的,文化其实也是这样的,很多东西消失了,是我们心里的痛。我们在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把它请回来、补救回来。我每次看到我的朋友的放在城市公寓房子马鞍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他在童年的梦的遗憾,用他自己能够,用他自己能够做到的方式补尝了,而且是草原上认识的朋友亲手为他做的。所以说,历史会消失,我们眼前很多丰美的文化都会消失,可是当我们现在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论他,我们想念他,我们互相交换他,我们对这个文化悲与欢的时候,它就会回来,就会回到我们心里,跟我们在一起。它消失了吗?它其实没有离开。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想这是草原上的阳光。
有一位希拉导演,他有一部片子叫《永远的一天》,反映了不会母语的诗人回到草原,他去收集字汇,他跟每一个人要你告诉我一个字,然后你再告诉我一个字。人们听说有一个人想要字汇,有人坐船来、有人坐路来的、每个人送给他一个所知道的很宝贵的字,最后这不会母语的诗人用他所收集的字汇写成了一首歌颂故乡的诗。有一天看到这个电影忽然发现跟我自己的感觉很像。我好像从来没有在草原上住过,但是和每一个朋友说他在这个草原上生活的细节的时候对我都是一个收获、是一个喜悦。
有一位知青在30年以前在草原上生活过,其实好几位在北京的,他们自己叫二蒙古,其中有一位和我说:你知道吗?其实骑马的时候骑母马最舒服了,因为他的背很柔软,骑公马就硌一些,骑老马的时候就硌坏了。我觉得好棒呀,在书上就没有人告诉你母马的背很柔软的,这是生活过的人和你说,可是在草原上是不能随便骑母马的,牧人都很心疼母马,母马要准备怀孕、要生产呀,不能骑。他说最舒服的骑在母马的背上,说完以后,好像我已骑在母马的背上了,我感觉整个人就呆了,然后他又说草原上很奇怪忽然之间开满了花,有一天傍晚是时候我骑马经过,整个草原全部开满了粉红色的花,那样一个傍晚,那样一个草原上开满粉红色的花。他在讲的时候我好像出骑在母马的背上,慢慢走过开满了粉红色花的草原。所以我想我的回家,我的这种所谓的执迷不悟,其实是为了收集所有我没有办法得到的细节,所以我要感谢每一位朋友,或者是我听的,或者是带我亲自体验的,或者改正我的错误的,都是引导我回到家乡的好朋友。
我要讲的最后一章,也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我亲身的事情,我画油画的时候想要休息的时候我就画一些小树,有时候是棵小的树,有的时候有很长很长的影子,那个影子有些不太像了,有这么长的影子吗,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很长的影子我心里说舒服,后来有一次中油画的画展里面,那个时候是比较早,我母亲还在的时候,我从欧洲回到台湾的第一次油画展览,我画了一张象海景的,我画了一些树,然后是丘陵、树的影子是长长的,心里的风景。有一位叔叔,他姓“海”,他是卫拉特蒙古人在台湾住,跟我母亲一起看这个画,那我在旁边听,这位叔叔的汉话很不好,所以他就很简单的和我母亲说,他说这好像我们老家,他说这看了想哭,他就说这么简单,那个时候我就在他的后面,我跟各位坦白讲我那时候真是不以为然,这是我自己心里想的风景,等我自己到了家乡,我看到这个场景,我到了鄂温克里面的山坡上面,看到那里一棵树、孤单的,那个就是我的油画,我在卫拉特蒙古人海叔叔新疆的巴音布鲁克、在博尔塔拉、在他的家乡一定有过同样的风景,这个时候我发现,原来我心里的风景,是所谓你表面看到我的心里的风景呢?还是我那个心里的他那个风景?这是我今天要向各位说的,我相信这个土地本身给我们的东西不只是表面的、眼前的。我觉得我好像是回来寻找,用我心的深度、用这个土地和这个文化氛围的广度、用这个时间,也许十几年、也许是我半生几十年的时间、也许是几千年的时间,我慢慢的在蒙古高原上找到我心里的坐标,找到它的位置,为什么现在觉得自己很自然,很多事情很从容,不怕你笑我,不怕你们说笨,不怕你说我错误,因为我觉得好像心里的那个它已经能够慢慢的跟我融合在一起了,所以我会变的很从容,可以说比较勇敢。一般来讲,一个人不可能去夸自己的,但是我想跟各位说:“我夸得不是我,我想夸的是任何一个离散在组群之外的生命所经过的这一切”。
|
|
上一个项目:
葛健(内蒙古仕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下一个项目:
陈光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
返回上级
|
 |
| 点击数:32509 录入时间:2006/3/25 【打印此页】 【关闭】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