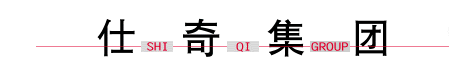元代的哈剌和林教育
王风雷(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主任、教授)
摘 要:元代的哈剌和林(Qara---Qorum)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故址在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ayimaq)额尔德尼召北。从1220年到1259年,在这短短的40年的时间里,哈剌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都城,云集了东西方的各色人种,可谓盛况极一时,扬名中外。1260年以后,随着忽必烈政治中心的转移,哈剌和林也就失去了其往日的辉煌,逐步降格为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和林宣慰司、和林等处都元帅府、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和林总管府、和林路和林行省治所,后来又成为岭北行省治所。然而,整个蒙元时期,哈剌和林的教育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形成了漠北地区的一个文化亮点。本文依据各类史料,就哈剌和林教育的渊源、脉络、走势及其特色进行了深入探讨,结论是,草原深处的教育达到了相当高的层次,并且对草原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元代 哈剌和林 教育
元代的哈剌和林(Qara---Qorum)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它的故址在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ayimaq)额尔德尼召北。从1220年到1259年,在这短短的40年的时间里,哈剌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都城,云集了东西方的各色人种,可谓盛况极一时,扬名中外。1260年以后,随着忽必烈政治中心的转移,哈剌和林也就失去了其往日的辉煌,逐步降格为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和林宣慰司、和林等处都元帅府、和林等处行中书省、和林总管府、和林路和林行省治所,后来又成为岭北行省治所。
纵观历史的变迁,哈剌和林的教育始终遵循着它应有的规律,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据史料记载,哈剌和林地区具有以下几种形式的教育:
首先,蒙古兴起之前,在哈剌和林地区活动的北方游牧民族当中,突厥人较早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因而他们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特色。据史料记载,突厥人在鄂尔浑河流域活动比较频繁,并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留下了很多文化遗迹。《周书》(1)(p910)和《北史》(2)(p3288--3289)上都以同样的方式说,突厥的“字书类胡,而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记”。实际上,史书出现这种记载的具体时间为魏废帝二年三月,即公元552年三月。另据《北齐书•斛律羌举传》载,大约在武平末(570—575年),“代人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作突厥语翻《涅盤经》,以遗突厥可汗,勅中书侍郎李德林为其序”(3)(p267)。遗憾的是,由于战乱及兵火,这些经卷早已散佚,没能得到流传,因而后人也只能凭着想象去推测其大致概况了。但是,以上信息确切地告诉后人,至少在公元552年的时候,或者更早的时候,突厥人已经创制并使用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对此,著名的历史学家林幹先生认为,突厥文大约在公元五世纪时创制和开始使用(4)(p159)。后来人们在鄂尔浑河流域或其他地区陆续发现并解读的暾欲谷碑(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阙特勤碑(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苾伽可汗碑(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翁金碑(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阙利啜碑(建于八世纪)、磨延啜碑等突厥文碑(4)(p245--286),对我们全面了解古突厥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值得一提的是,耶律铸在其《双溪醉隐集》卷二《取和林》的诗文中,指出了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和阙特勤碑的准确位置,而且他根据碑文纠正了史籍上对勤字的错误记载,是“勤”而不是“勒”。
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任何一种文字的传承,它都需要有一个与之相应的教育。因此,没有教育,文字的延续、发展和传播,都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笔者认为,突厥文的创制和使用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育,它用间接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生活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古突厥人的教育,而且也有力地证实了古突厥人的学校教育所达到的那个历史水准。当然,突厥人的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学校教育的规模、形式、手段和方法,甚至也决定了其教育场所的分散性和不固定性。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的限制,在当时的突厥人当中,能够进入所谓的学校,接受突厥文教育的人还是十分有限的,只有那些奴隶主贵族子弟才有这种可能。这与古代中原地区 “学在官府”的史实基本相近,广大奴隶的子弟基本上与这种教育无缘。
除了突厥,契丹人在鄂尔浑河流域的活动,也是很频繁的。陈得芝先生认为,辽朝在这一地区建有镇州、防州、维州、招州。这样,这些地区应该有相应的教育,而且也通行过契丹文字,但由于笔者的能力所限,再加上文字资料的缺乏,很难进行深入考述。至于元以前活跃于这一地区的其他游牧民族,未予以考虑。
其次,大蒙古国时期,由于各色人种的云集,在哈剌和林的教育当中怯里马赤(ΧЭЛМЭРЧ)——译史的培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应该说,这是由当时的社会需要所决定的。据史料记载,太宗乙未年(1235年),城和林,作万安宫;丁酉(1237年),治伽坚茶寒殿(Gegen cagan ordu),在和林北七十余里;戊戌(1238年),营图苏胡迎驾殿(Toshu ordu),去和林城三十余里(5)(p1382--1383)。清代的大学者张穆在他的《蒙古游牧记》中,用大量的史实对《元史•地理志》记载的“太祖十五年(1220年),定河北诸郡,建都于此(和林)”之说(5)(p1382)予以了否定(6)(p143)。笔者认为,张穆的确发现了一个历史记载的矛盾之处,然而他所得出的结论,似乎缺乏更深层探究。对此,陈德芝先生的的考证,更符合历史事实,他认为成吉思汗曾经在这一地区设置了一个斡耳朵(7)(p36)。对于定都哈剌和林的年代问题,除了《元史》,其他好多资料都说始于太祖十五年(1220年)。笔者认为,元人的记载还是比较准确的,而且记录者与史实发生的时间间隔不是太长,其错误率应该是比较低的。因此,大蒙古国的建都哈喇和林城的确切年代为太祖十五年(1220年),而真正大兴土木动工兴建始于太宗七年(1235年)。
在当时,哈剌和林作为大蒙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对东西方的各色人种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因而人们从四面八方都汇聚到这座崭新的城市,寻找各自的发展机会。当然,那个时候来哈剌和林的人,有的是被动、被迫而来,这类人是作为蒙古军的俘虏被押解过来的,而有的则是为完成一项使命主动、自愿来蒙古高原的,这类人主要是以商人或个别使者为主。从种族结构看,哈剌和林城里除了有蒙古人之外,应该有汉人、土番、唐兀、女真、契丹、党项、吉利吉斯、水达达、高丽、畏兀儿等人种。这些仅仅是北中国的一少部分种族而已,其中还不包括南中国的诸蛮夷。另外,从西方的种族分布情况看,在欧洲大陆上被蒙古征服的或未被征服的种族有,斡罗斯人、摩尔忒瓦人、孛剌儿人(大不里阿耳)、巴思哈儿惕人(即大匈牙利)、巴罗昔惕人、萨摩耶德人、阿兰人、薛儿客速人、可萨人、希腊人(人)、孔士坦丁堡(人)、亦比里人、哈希人、不鲁塔赤人、昔克赤人、谷儿只人、阿美尼亚人和突厥人(8)(p57);而在中亚地区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伊朗人、克什米尔人。我们不敢断言,上述的各色人种都来过哈剌和林,但是,他们中一少部分人来大蒙古国都城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蒙古行记和鲁不鲁乞的东游记中得到答案。因此,在哈剌和林城里,各色人种间的相互交流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这在客观上就需要一批甚至是一大批的口译人员——怯里马赤,使之在各色人种间的交流中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众所周知,各色人种之间的近距离交流需要口译人员,而远距离的交流则需要笔译人员——必阇赤。这样,哈剌和林城的译史教育分为两个层级:一为口译人员的培养;二为笔译人员的培养。无论哪一层级的译史,他必须精通多种语言,否则它就很难适应社会的需要,这一点是由当时各色人种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到了天历二年(1329年),元朝政府在岭北设行枢密院的时候,充分考虑了这一地区各色人种间的语言交流问题,因而在该机构中专门安排了蒙古必阇赤四人,怯里马赤一人(5)(p2157)。这说明天历年间(1328——1330年)岭北地区各色人种的杂居也非常普遍,他们之间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和林金石录》里,我们还能找到书吏王克弘、译史□□直、译史□朵里别反、译史□也先等题名,与正史上的记录基本吻合。那么,大蒙古国时期的译史是怎样受训的呢?对此笔者认为,他们大多是在特殊的多语环境和多语实践中锻炼成长的,相反在专门的学校受训者,很可能为数不多。这一点笔者在新疆的伊犁和博尔塔拉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后,从当地蒙古人身上得到了证明。那里的许多蒙古人不仅会讲蒙古语,而且会讲汉语、维语、哈萨克语,所有这些他们都不是在学校里掌握的,而是在多语环境和多语实践中学到的。
第三,在哈剌和林的教育中,宗教教育占一定的比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蒙古国组织的一场神学上的辩论,可以得到证明。组织神学上的辩论,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也是一项文化教育工程。随着人员往来的增多,特别由于是各色人种的汇集,哈剌和林城确确实实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中心。这里的多元文化不仅体现在各色人种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上,而且还体现在他们所信仰的不同宗教上。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统治者所实施的宗教政策是比较宽容的,因而萨满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在哈剌和林都有一定的席位,且有大量的信徒。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它历经沧桑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得到传播和延续,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教育,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育。
就拿古代蒙古人的萨满教来讲,它首先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力量,它要求人们崇尚英雄,一往无前。为此,一些学者认为,蒙古铁骑之所以能够横扫欧亚大陆,其中萨满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见,萨满教对蒙古人的影响是显性的。除了精神方面的影响,萨满在科学文化的传播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蒙古社会,萨满既是一个医师,又是一个文化工作者。他们一方面用原始的方法为百姓解除病痛,另一方面也为蒙古族诗歌及舞蹈的繁荣,作了大量的工作。萨满在公共场合念诵的祝赞词是很有特色的,这在蒙古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萨满舞让人耳目一新。今天在内蒙古地区流行的安代舞就是源于萨满舞,除此之外,在其他类型的蒙古舞当中也能够看到萨满舞的踪迹。
佛教在哈剌和林具有很高的地位,早在太宗八年(1236年)的时候,蒙古统治者就为僧人提供了专门的活动场所。耶律楚材的“龙沙玄教未全行,故筑精蓝近帝城。须仗檀那垂手力,一轮佛日焕然明”的诗句(9)(p322),向世人介绍了和林地区开始兴建佛寺的基本情况。另据兴元阁碑的记载,从乃马真皇后称制(1242—1245年)到元顺帝(1333—1368年)的126年的时间里,和林的佛寺呈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为此,蒙古统治者分别于宪宗丙辰(1256年)、至大辛亥(1311年)、至正壬午(1342年)共三次投巨资修缮了和林的佛寺(10),使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毫无疑问,这座佛寺里的高僧们面壁修炼,讲经授徒,翻译经卷,以其辛勤的劳动弘扬了佛法。
据史料记载,唆儿忽黑塔尼别吉“尽管她是一个基督教信徒,她仍然竭力促进默罕默德教律的兴隆,向伊斯兰教伊玛目和洒黑们赐予大量施舍和慷慨馈赠。她给出一千银巴里失用来修建不花剌的一所伊斯兰教学校,……她吩咐购买了几座村庄,把它们捐赠给这个伊斯兰教学校作为不动产,在那里聘请和招收了教师和学生”(11)(p236)。据此可以推断,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多,当时在哈剌和林也应该有类似的学校。
笔者认为,就基督徒的传教而言,它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育,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教会学校的发展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蒙古国时期也不例外。史书上说,“蒙哥合罕以其智慧的完美和远见卓识,卓异于其他蒙古君王,他曾解答欧几里德的若干图解” (12)(p73)。应该说,蒙哥合罕这一才干的形成与基督徒的教育影响是分不开的。
至于道教它对蒙古人的影响就更早了。太祖十六年辛巳(1221年),丘处机在雪山拜见成吉思汗,并向他讲授了“长生久视之道”的秘诀——“清心寡欲”,对此大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5)(p4524——4525)。这样,丘处机就成了皇子们的师儒,而且享有了特殊的权利。后来,太宗五年癸巳(1233年)和太宗六年甲午(1234年)的时候,燕京的夫子庙学里基本上是由道人冯志亨和仙孔八合识李志常等人负责教务,而且延续到了宪宗元年辛亥(1251年)(13)(p197--199)。如此看来,至少在蒙哥以前在哈剌和林的教育中道教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
第四,元代科举考试的发源地是哈剌和林,这是因为,太宗九年(1237年)的设科取士的政令,是大蒙古国定都哈剌和林的那一历史时期发布并实施的。笔者认为,当时大蒙古国许多重大的政治决策,应该是在哈剌和林定夺的,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蒙古最高统治者从这个斡耳朵到另一个斡耳朵进行迁徙的一些基本事实。然而,哈剌和林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也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因此大蒙古国设科取士这一重大决策的出台与这座新兴的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总而言之,太宗九年(1237年)的设科取士,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这在大蒙古国的初创阶段,是一个首创,同时也为以后元仁宗(1312——1320年)全面推行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汉族知识分子的入士,带来了一线希望,为夯实蒙古统治的根基进行了一次有效的尝试。另外,本次的设科取士还标志着蒙古统治者对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与此相伴,蒙古统治者治理汉地的政策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不杀的问题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农牧间的冲突有所缓解,汉地的农业得到发展。后来,随着政治中心南移,特别是在元代的科举考试当中,哈剌和林或岭北行省一直行使着其组织乡试的职能,为高一级的考试选送了一批合格的人才。据史料记载,元朝政府明确规定了岭北行省乡试录取的具体名额,即蒙古取三名、色目取二名、汉人取一名(5)(p2021),一共取六名。当然,当时岭北行省的乡试是在和林或和宁开考的,这一点,恐怕没有多大疑问,但是还有很多问题不是十分清楚。为此,笔者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资料太少或者说没有,因而很难进行深入探讨。也许是地域的缘故或者是南人降服的时间较晚的缘故吧,元代的岭北地区南人所占的比例相对低一些,因而在岭北地区的乡试中未分配南人的名额。这说明南人还没有完全渗透到这一地区。至于岭北行省乡试答卷的语种问题,笔者在《补论元代科举考试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有所述及,这里就不再赘述(14)。
在哈剌和林的教育中,蒙古语言文字的教育占很大的比重。八思巴字颁行之前,这一地区主要运用畏吾字;八思巴字颁行之后,该地区的教育也开始使用蒙古新字,但畏吾字仍有一席之地。岁甲子(1204年),铁木真灭乃蛮后,他让深通本国文字的战俘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5)(p3048),这表明蒙古人不但有了自己的文字,而且也有了相应的教育。然而,周清澍先生认为,从塔塔统阿到搠思吉斡节儿的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蒙古人真正用畏兀字留下来的资料,包括碑文也是有数的那么几个,不是很多。笔者认为,周先生的这句话是正确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道布整理、转写、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中得到答案(15)(p1--23)。总的来看,在道布先生的大作中,与哈剌和林相关的畏兀字碑或牌也只有三块,一是列宁格勒所存1225年移相哥刻石(或称成吉思汗石)文字五行;二是1240年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三是贵由皇帝的令牌。值得一提的是,道布先生在书中对这三块碑牌都付了照片或复印件。相比之下,蔡美彪先生在研究1240年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时,只提到有三行畏兀字并做了注释,而没涉及其具体内容(16)(p7)。如此看来,在哈剌和林地区或在岭北行省,人们确实用特有的方式学习并使用畏兀字,为今日之蒙文的形成发展做出了贡献。随着蒙古新字的颁行(5)(p4518),至元六年(1269年)七月,政府就下令设置了诸路蒙古字学(5)(p2028)。这样,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当地的官员们贯彻元朝政府的政令,也在这一地区设立了蒙古字学。在《和林金石录》里,有“蒙古教授郝完泽上阙不花”、“蒙该字只有上部而下半部脱落□学教授裴祐”的记载,在“三灵庙碑”上也有六字蒙古国书(17),可惜未提供蒙文原件。这说明,当时在哈剌和林确实有过蒙古字学。另外,蒙古国达尔汗乌拉艾(爱)马克达尔汗市东北76公里处,在灰腾河畔一山阳岩石上1980年发现了八思巴文(9行)和回鹘式蒙古文(11行)墨书二则(18)(p510)。这一资料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岭北地区蒙古字学的发展的情况,同时也为人们了解该地区八思巴字和畏兀字并行的情况,提供了帮助。
第五,在哈剌和林的教育中,儒学、医学和阴阳学教育还是比较突出的。对于这一点,当时被派遣到和林的官员和师儒们,为发展当地儒学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当时蒙古统治者从汉地招募了很多工匠。这样在哈剌和林地区的各色人种当中,汉人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汉人聚居区(19)(p41)。这种情况为当地儒学和相关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纵观蔡美彪先生的《元代白话碑集录》,蒙古统治者在定都哈剌和林期间向汉地发布的政令,能够以碑文的形式保留至今的有25块。笔者认为,这些资料虽然不能直接反映哈剌和林地区儒学发展的情况,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有助于人们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忽必烈入继大统后的近百年的时间里,哈剌和林或岭北地区儒学的发展,基本上与朝廷向该地区委派的要员们发生着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年)七月,元朝政府“罢和林宣慰司,置行中书省及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和林总管府。以太师月赤察儿为和林行省右丞相,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为和林行省左丞相,依前太傅、录军国重事”(5)(p483—484)。哈剌哈孙的到任为这一地区儒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这是因为,过去他在教育方面曾经有过突出的业绩,“其在中书也,引儒生讨论坟典,至尧舜文武之为君,皋 稷契伊傅周召之为臣,(叹)曰:‘人生不知书,可乎?’乃馆士,教其子学”(20)。这些在《元史•哈剌哈孙传》里,也有粗略的记载(5)(p3293)。作为一个人,不读书就是不行,要读书就必须抓教育,这便是哈剌哈孙的理论。有思想有作为的人到哪儿都一样,他到了哈剌和林之后,也为当地儒学办了一些实事。“孔子庙,故丞相顺德忠献王所筑,未成而王薨”(21),壮志未酬身先死,可见,哈剌和林的孔庙或曰儒学是由哈剌哈孙着手奠基的。对于这一点,元末儒臣许有壬也在他的《至正集》中也有相同的记载(22)。除了哈剌哈孙,对哈剌和林儒学发展有贡献的人就是苏天爵的父亲苏志道了。延祐四年(1317年)苏志道出任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直至延祐七年(1320年)辞归,去世。据载,他在岭北行省任职期间创造了不朽的业绩,特别是在赈济灾民恢复生产、法律诉讼振兴教育等方面政绩显赫,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普遍好评。苏志道在个人的学习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和林既治,事日简,乃即孔子庙,延寓士之知经者讲说,率僚吏往听,至夜分休”(21),为边远地区士风的转变开辟了新路。值得一提的是,苏志道继承了已故丞相顺德忠献王哈剌哈孙的遗志,捐俸铸就了孔庙(22)。因此,哈剌和林的儒学发展史上,哈剌哈孙和苏志道的功劳最大,他们的英名将永远载入历史史册。哈剌哈孙和苏志道的业绩,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使他们对哈剌和林的儒学给予了关注和扶持。这主要表现在,至顺三年(1332年)十月,蒙元统治者“命江浙行省范铜造和宁宣圣庙祭器,凡百三十有五事”(5)(p812)。另外,元末文化名人危素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出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明年(1365年)弃官”(23)。从理论上讲,危素与哈剌和林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可惜的是,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因而对此很难进行深入探讨。
据史料记载,在当时的哈剌和林儒学里,至少有以下几名师儒,从事过教育教学工作。他们是:和林路儒学正金陵余良辅、儒学教授□□、学正刘枌、学□教子长、和林兵马司儒学正张思明、和宁路儒学正彭诣等(17)。除此之外,至正十五年乙未(1355年)之前,“古田主簿鄱阳萧澄尝为和宁学官”(24)。这样,元代岭北行省的儒学的学官配置,与其他地区的学官配置基本一致,没有太大的差异,而且南方学者在此任教已成为一个特殊现象。根据上述师儒们的题名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哈剌和林的儒学规模,应该说是不小了。
除了儒学,哈剌和林的医学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据史料记载,哈剌和林的医学或曰三皇庙留有两块残碑。第一块残碑是由“上阙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监丞张益撰,上阙省参知政事刘塔失帖木耳篆,上阙省左右司都事李塔失帖木耳书”(17)。该碑主要传递了一下两方面的信息:它告诉后人三皇庙的具体位置在“省治之南”,其建筑规模为“建庙四楹”;泰定末(1324—1328年),当地官员“欲以官帑易而新之”,但落实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第二块残碑是由“捏古柏立石,路吏李仲宗督工,和宁路医学教授贾此处还应该有字但原文就没有董役,儒学录苏仁、兵马司吏目陶元璟模镌”(17)。该碑的主要内容为:三皇庙是由上阙彻都协力施俸经营的,而且落实的速度非常快;三皇庙是在“故址广而大之”,“新规制视昔迴然不同”;经始于至顺元年(1330年)春,落成于至顺二年(1331年)之夏。一方面哈剌和林的医学之建筑因年久需要修缮,另一方面其规模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当地政府投了巨资使它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蒙古草原。与医学教育的发展相适应,在当时的哈剌和林有医学教授刘明、学正(医学)贾福、医人周中信、张翼刘润甫、常士□、王仲贤、医学正李叔亮、宋郁、高侃、惠民良医杨仲文、省医胡景朂、武舜谦、李贵等专业人员(17),他们在救死扶伤以及在医学科学的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哈剌和林的阴阳学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在当地的资料当中出现了阴阳学正张允恭、阴阳学正刘进、张光、阴阳人朱诚翁、王明见、王郎等人的题名(17)。由于资料的缺乏,对这一问题我们很难进行深入探讨。
第六,与屯垦戍边相联系,哈剌和林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因而当地的农业技术教育,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陈得芝先生认为,哈喇和林地区的屯田始于辽代,这主要与当时在该地区建置的城郭有着密切的联系(7)(p35)。其实,蒙古人作为畜牧业生产的辅助形式,从事农业生产的历史比这还要早。从蒙古国南戈壁省的图古力克、希力图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舂米用具——石臼和石碓(25)(p215)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在今天内蒙古东部地区也能看到这样的石臼,只是后人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把它放在井台上当作饮马槽来使用的多了。十三世纪初,篾儿乞部落仍然用这些器具进行舂米(阿兀儿——那都别)(26)(p537),加工着他们所食用的米面,而且他们还经营着少量的塔里牙(tariya)——农田(26)(p693)。后来,帖木真“掠其资财、田禾以遗汪罕”(5)(p6)。这些情况,与宋代的李心传“熟鞑靼尚能种穄秫,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的记载(27)基本一致。
不管什么时代,粮食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成吉思汗为解决给养,在农业经济的发展方面费了一番苦心。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征时,听从哈剌亦哈赤北鲁的建议,开发了别失八里(汉代的北庭,故城在新疆吉木萨尔境内)以东独山城地区的农业,后来1225年他亲眼看到这一地区“田野垦辟,民物繁庶”的时候,大喜(5)(p3047);在此之前七年壬申(1212年),他还“命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戍守之”(5)(p2964),对于这一史实许有壬也作了明确的记载28。1221年,丘处机到达镇海八剌喝孙的时候,那里的屯田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陈得芝先生对镇海(称海)城的具体位置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证(29)(p55-60),据此笔者查阅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蒙古国地图后发现,镇海城的大概位置在于今天的蒙古国科布多以东的哈腊乌斯湖(Xap-yc)和哈腊湖(Xap-Hyyp)的中部平原,这里的气候、土壤、水利都比较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除了镇海城,当时和林附近的农业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张德辉的《纪行》当中得到证明。岁丁未即贵由二年(1247年),忽必烈在漠北召见张德辉,这样他记录了沿途的见闻,为后人留下了可信的资料。他说:和林的“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有蔬浦。时孟秋下旬,糜麦皆槁”,绕过忽蘭赤斤(红耳ulagan cigin)“乃奉部曲匠民种艺之所”(30)。可见,和林城周边的农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而且水利设施日趋完备。
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以后,蒙古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哈剌和林地区的屯田,为这一地区的稳定提供了物质保障。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政府徙生券军八十一人屯田和林(5)(p156);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六月,从憨答孙请,移阿剌带和林屯田军与其所部相合,屯田五河(5)(p267);大德元年(1297年)四月,给岳木忽而所部和林屯田种(5)(p411);大德五年(1301年)八月,政府采纳秃剌铁木而等人的建议,为和林屯田军广其垦辟,提供了农具(5)(p436)。当然,元代哈剌和林地区的屯田也有一定的起伏,甚至出现了田野荒芜“屯耕事即废”(31)的现象。延祐五年(1318年)五月,元朝政府复置称海、五条河屯田的史实(5)(p602)就说明了这一点。据史料记载,对哈剌和林地区的屯田有贡献的人首推哈剌哈孙,而且他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当地的粮食丰收奠定了基础。“称海屯田久废,(哈剌哈孙)重为经理,岁得米二十余万斛。益购工治器,择军中晓耕稼者,杂教不落。又浚古渠,溉田数千顷。谷以恒贱,边政大治”(32)(p60)。除了哈剌哈孙,对哈剌和林地区的屯田有贡献的人就是郭明德了。大德六年(1302年),郭明德以(和林)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的身份,就海都犯边问题提出了几条应对策略。其大意为(33)(p170—171):一、安边之策,务在屯田积谷,且耕且战,自古如此;二、必须降低从内地往和林运粮的成本,并提高它的经济效益;三、和林之北,地宜麦禾,每军抽步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四、和林寒苦,汉军不能冬,让蒙古军之强壮者戍边,贫弱者教之稼穑,以相资养。五、置田官,起仓廪,严赏罚,强化粮食储运;六、训练兵甲,高城深堑,提高元军的作战能力和防御能力。郭明德提出来的这些对策建议,对消除北部边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措施得力,至大二年(1309年)二月的统计数字显示,以和林屯田去秋收九万余石(5)(p510),这个数字恰好与“岁得米二十余万斛”的记载相吻合的。与此相对应,还有一个数字告诉我们岭北省屯:称海五条河四千六百户,六千四百顷(34)。数字不大,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当时哈剌和林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从隶属关系上讲,益蘭州(今俄罗斯图瓦自治州境内乌鲁克穆河南支流埃列格斯和麦日盖河汇流处)也属于岭北行省的管辖范围。“至元七年(1270年),刘好礼迁益蘭等五部断事官,以比古之都护,治益蘭。其地距京师九千余里,民俗不知陶冶,水无舟航。好礼请工匠于朝,以教其民,迄今称便”(5)(p3925)。这样刘好礼在教民种植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纵观史料记载,蒙古统治者一方面为开发哈剌和林地区的农业,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另一方面在抵御自然灾害赈济难民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早些时候的古代典籍里,“包犧氏没,神农氏作,斵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35)(p64);“尧聘弃,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妍营种之术。三年余,行人无饥乏之色,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姓姬氏”(36);“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人民育”(37)(p39);“故尧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民也,水处则渔,山处则木,谷处则牧,陆处则农”(38)等记载。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学者们,把上述的记载统称为教育。据此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断,哈剌和林的农业技术教育与元代屯垦戍边的历史举措混杂在一起,很难进行严格的划分。当地的各色人种,特别是蒙古族农牧民在生产的实践中,学会并掌握了种植技术,进而汉地或西方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了有效的推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草原的沙化。
总之,元代哈剌和林的教育,与内地的教育相比,还是比较闭塞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留下来的东西也不多,而且十分零散。近几年的考古资料给人们提供了一些信息,但真正教育方面的资料还是比较缺乏的,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研究本课题的难度。因此,目前笔者也只能研究到这个程度。
注释:
(1)(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
(2)(唐)李延寿等撰《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3)(唐)李百药撰《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
(4)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明)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
(6)(清)张穆撰《蒙古游牧记》,张正明 宋举成 点校,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陈德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专辑《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9),1985年3月出版,31——44页
(8)(英)道森编,吕浦译,周良宵注《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9)(元)耶律楚材著《湛然居士文集》,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
(10)(元)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十五《勅赐兴元阁碑》;也见许有壬《圭塘小稿》卷九《勅赐兴元阁碑》,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1)(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二卷,余大钧 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2)(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三卷,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3)(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4)王风雷《补论元代科举考试中的几个问题》,载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11——18页
(15)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巴•巴根校,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16)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17)《和林金石录》,(清)江标辑《灵鹣阁丛书》
(18)呼格吉勒图 萨如拉 编著《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汇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9)韩儒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
(20)(元)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二十五《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刘敏中撰》,四部丛刊集部
(21)(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五《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朗中苏公墓碑》,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22)(元)许有任《至正集》卷四十七《敕赐故中宪大夫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朗中赠集贤直学士亚中大夫轻车都尉追封真定郡侯苏公神道碑铭》,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3)(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五十九《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24)(明)危素《危太朴集》卷十《艾蜚英赤纳思百韵诗序乙未》,说学斋稿
(25)(蒙古)X•桑琵乐登德布《蒙古族风情》(蒙文),那顺乌力吉、道尔吉转写,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
(26)《蒙古秘史》,巴雅尔复原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十《鞑靼款寨》,函海本
(28)(元)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十《元故右丞相怯烈神道碑铭》,三怡堂丛书本
(29)陈得芝著《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0)(元)张德辉《纪行》,见(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一百《玉堂嘉话卷之八》,四部丛刊集部
(31)(元)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八《跋虞司业撰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文》,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32)(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中华书局,1996年版
(33)(元)苏天爵《滋溪文稿》,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
(34)(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一《经世大殿序录•屯田》,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35)《周易本义》,朱熹注,见《四书五经》(上),宋元人注,中国书店,1985年版
(36)(后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四部备要史部
(37)《孟子》,朱熹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8)《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汉)高诱注,四部备要子部
参考文献:
(1)伯希和 著 米济生 译《哈剌和林札记》,载于《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新编第26、27辑(总第51、52辑),1983年5月,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
(2)(蒙)德•纳旺《哈剌和林出土的铁器》,载于《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新编第35辑(总第60辑),1984年11月,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
(3)(苏)л•A叶甫邱霍娃 《哈剌和林出土的古代中国陶器》,载于《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9辑,1965年4月,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研究室编印
(4)白石典之《日蒙合作调查蒙古过哈拉(剌)和林都城遗址的收获》,载于《考古》,1999年第8期
(5)间接参考了苏联学者吉谢列夫,C•B《古代蒙古的城市》,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
(6)蒙古国博物馆提供的万安宫复原图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