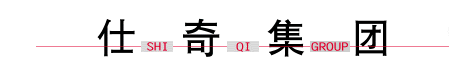丹僧叔叔:
一个喀尔玛克蒙古人的一生
文/席慕蓉
【1】
一直想要提笔写出丹僧叔叔的一生,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开始。
这几年来,常常会带着幻灯片去演讲,向台湾的听众介绍我所看到与知道的蒙古高原,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候,一张幻灯片在黑暗里停格,而我在黑暗里滔滔不绝地诉说,仿佛在长久的时间与广漠的空间之中,有千头万绪都奔涌而来,都争着要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之内现身、解释与告白。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在台湾的教育之中,有关于北方民族的历史人文,除了其中极少的经过挑选了的资料之外,其他一切都是空白,这就让我在介绍的时候变得非常困难。本来应该是只说重点,突出精彩的部分,可是如果听众对一切的背景资料都毫不知情的时候,又怎么能够明白那重点的悲喜之后的远因与近果呢?
写丹僧叔叔,也是如此。
我当然可以先从1966年写起,那年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但是,如果要清楚地说出他之所以如此的重要环节,就又必须从1630年开始写起。
所以,我只好话分两头……
【2】
先说1966年。
那年夏天,父亲带我去丹僧叔叔的家。
他有妻有子,并不是一位僧人,“丹僧”这两个字,只是他名字的蒙音汉译而已,但是如今又觉得满贴切的。
他是父亲的朋友,比父亲年轻几岁,所以我就这样称呼他。
那时,父亲在慕尼黑大学教书,我在布鲁塞尔读书,姐姐和妹妹也都在欧洲。所以,一到假期,我们就会坐火车南下或者北上地彼此探望。
去慕尼黑的时候,父亲有时会带我们去市郊几个蒙古族人的家里做客。
其实,那时我对丹僧叔叔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这几个蒙古族家庭都住在郊外廉价的国民住宅里,房子不大,主人都很好客,每次见到我都会紧紧地拥抱,在我脸颊上亲了又亲,给我吃很多用羊肉烹调的大菜,笑着劝我喝酒,然后又唱歌又跳舞的,热热闹闹地过一晚。去了这家,就一定要答应再去另一家,不然的话,就是两三家凑到一家来联欢,所有的孩子也都跟着父亲过来,高高低低大大小小地挤满了一屋子,那种热情和欢乐,才是让我印象深刻的记忆。
在当时,我也注意到了,虽然同是蒙古族人,父亲和那几位叔叔的交谈中常常要夹杂着英文才能说得通。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他说:“他们是喀尔玛克蒙古人,最早是住在新疆那一带的,口音和我这个察哈尔蒙古人很不相同。而丹僧他们又是从小在俄国长大的,有些单词我实在听不懂,就只好用英文来帮忙了。”
那天,是我第一次听到“喀尔玛克”这个词,父亲说,这词的意译是“留下来的”的意思,也有人译作“余留者”。
父亲又说:“喀尔玛克蒙古人虽然可说是远离家乡的流浪者,可是对于蒙族的老规矩却一点也没忘,真是不容易啊!”
【3】
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重要的部族。在中心地带,散步在戈壁南北的是喀尔喀蒙古人,也就是我们比较常听说的内蒙古和外蒙古人(这之下再细分,才会有我父亲所属的察哈尔盟,或者母亲所属的昭乌达盟等等)。在东部嫩江流域的是达呼尔蒙古,在北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边的是布里雅特蒙古,在西部以天山山脉为中心的是卫拉特蒙古(或称瓦剌)。
卫拉特蒙古世居新疆北部,在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周边一直到乌鲁木齐和阿尔泰山之间,分成四部——土尔扈特、准噶尔、和硕特和杜尔伯特。16世纪末期,和硕特人跟随着他们的顾实汗去了青海,就是如今的“青海蒙古”的前身。而土尔扈特人从16世纪的1574年代开始,就逐渐计划西迁到中亚草原。
那时候的中亚草原上并没有任何政治与军事上的干扰,人烟稀少水草丰美土地辽阔,先驱的探路者一直抵达了伏尔加河流域,回报之后,1630年土尔扈特人就在和•额尔勒克的领导下,大举迁徙。他们陆续出发,用了好几年的时间,长途跋涉,终于定居在里海北岸的阿斯塔拉汗地区,在那一片无忧无虑没有任何威胁的土地上建立汗国,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好日子。
但是,18世纪开始,俄国国势强盛了之后,对于帝国南方这些游牧民族的地区开始有了染指之心,恶运就慢慢逼近了。
在一连串的高压统治与宗教迫害之后,土尔扈特蒙古人不禁又怀念起那在遥远的天山之上的故土了。
那时在家乡,多年争战的准噶尔部终于被清廷所灭,“数千里内,遂无一人”。消息传来,更坚定了他们想要回家的心。于是,1770年底,躲过了俄国官吏的监视,渥巴锡汗召集了王公贵族和喇嘛密商,决定全族“东返准噶尔故土”,并且以抵抗哈萨克人入侵的理由,开始集结土尔扈特军队。
多年之后,在天山山麓上的天鹅湖畔,一位土尔扈特的学者告诉我,他们自古以来,都自称是“天鹅的部族”,因为,土尔扈特人的性格一如天鹅,不喜欢争战,如果遇到强大的压力,就会展翅飞离,要到了威胁解除之后,才会再慢慢飞回来。
但是,在天上的飞鸟也许可以平安做到的事,在地上的土尔扈特子民却没有这么幸运了。
其实,当时什么都设想到了,什么都计划好了,甚至连出发的“良辰吉时”也都请喇嘛先挑好了,在年轻的渥巴锡汗英明的领导下,分布在伏尔加河两岸的20万土尔扈特人,可说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但是,残忍的上苍,却对他们开了个无法料想到的玩笑,那年冬天,伏尔加河竟然不肯结冰!
1771年1月5日清晨,天已亮、鸡已鸣、时辰已到,河西有7万土尔扈特人却怎么样也无法渡河。人马在两岸集结,消息已经走漏,如果再不走,必然会遭到全族灭亡的命运,渥巴锡汗终于含泪下令出发,东岸的16万多的土尔扈特军民向西叩首作别,踏上东返故土的长路。
我在这里先不说这近17万人的归乡之路是多么崎岖坎坷充满了追杀掠夺的死亡阴影,8个月之后,当他们终于抵达了故土之时,只剩下不到6万的零零落落一无所有的残破队伍,这就是西方史学家所说的:“历史上最悲惨的迁徙。”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那7万个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土尔扈特人的厄运,因为,他们就是丹僧叔叔的先祖。
1771年之后,这7万个留下来的土尔扈特人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喀尔玛克”(也有译作卡尔梅克),这是那些旁观者,也在中亚草原上生活的突厥人,半带戏谑半带悲悯地给他们取的名字。从此,这些“留下来的”人,终生都只能与悲苦共存。
【4】
1970年从欧洲回来之后,我和海北忙着开始工作,养育子女。居住在新竹或是龙潭乡下,都是偏僻的地方,不大能和朋友常常来往。倒是在几次台湾蒙藏委员会款待回台湾蒙胞的欢迎会上,见到丹僧叔叔,虽然都只是匆匆一会,仍然觉得很亲切。
不过,真正有机会与他深谈,却是要到了1991年的夏天了。
那年夏天,受一位在台湾学中文的喀尔玛克女孩娜塔丽之托,要我去访问丹僧叔叔在慕尼黑设立的喇嘛庙,如果我能拍几张相片回来,也许可以帮他申请到一点补助。
我答应了。于是,1991年6月14号的下午,父亲和我,再一次去探访丹僧叔叔。
奇怪的是,明明仍旧是同一所住宅,为什么给我的感受却与二十多年前的截然不同?那天下午有阳光,社区里也有绿树有草花,可是为什么却给我一种荒芜和寂寥的感觉,孩子们早已经长大了离开了,只剩下衰老的父母安静地坐在空空的公寓里,庭园依旧,岁月恍惚。
丹僧叔叔的心脏不好,走几步楼梯就要稍作休息,当然也更不能喝酒了。他本来就不高,如今身躯显得更加矮小,头发已经花白,好像比父亲看起来年岁还大。他带我们去参观喇嘛庙,其实,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一间佛堂的规模而已,却是几十年来,散居在欧洲喀尔玛克人的精神支柱。
佛堂在丹僧叔叔的住家附近,是一栋公寓楼房的二楼,从外观看跟普通的住家没两样,房门上只有一条小小的黑色门牌表示着德文“BUDDHISTISCHER TEMPEL”。进门之后有客厅和饭厅以及小厨房,佛堂在左边的大房间里,平时房门紧闭,只有祈祷的时候才会打开,好保持清净与尊严。虽然都是因陋就简的设备,但是一进入佛堂之时,却仍然会觉得心头一凛,那种深藏在漂泊者心中的虔诚,让眼前的佛像、供品、香烛和佛幡都平添了一层更加灿亮的光泽。
丹僧叔叔在我旁边向我详细地介绍这个喇嘛庙是如何由一位流亡在外的喀尔玛克喇嘛所创立的,又如何在战后的德国辗转搬迁,终于在慕尼黑停下了脚步。从1945年到1991年,将近有五十年的光阴了,尔丹僧叔叔从1948年开始,都担任照顾的责任,德国政府每年也有津贴,可以缴付房租和水电的费用。
原来供奉的佛像,是从1648年,当土尔扈特人陆续迁徙到中亚草原的时候。从天山故土的庙里请出来的。三百多年来随着他们的族群从新疆天山、中亚草原,从伏尔加河边一直走到了欧洲,在德国供奉了几年之后,1951年又随着一批被批准移民到美国的喀尔玛克人带到美国去了。如今这个佛堂里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像。
“但是,我们还留下了7个白银做的供杯。这也是当年土尔扈特先祖们离开天山的时候一起带着走的,到今天也已经有350年的历史了。”
丹僧叔叔把7个供杯都排在神坛之前要我拍照。那三百多年来一直被小心呵护的银质供杯上,一丝伤痕也没有,在灯光下闪耀着温柔的光芒。信仰,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当满身伤痕的喀尔玛克蒙古人来到佛坛之前,想必都能够从这些完好无缺的物件身上,得到极大的安稳罢。
【5】
1772年,在一次对抗俄国高压统治的革命失败之后,俄国凯瑟琳二世下令终止这些喀尔玛克人“汗”的称号与地位,把他们从独立的藩国降为帝俄子民。同时又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整合与“俄化运动”,分化和移民。
当初土尔扈特人力图避免,不惜举族迁徙的疑惧与忧愁,如今都变成真实的灾难,在伏尔加河西岸,这7万“留下来的”蒙古人只能以孤独与脆弱的肉身来承担。
惟有灵魂依旧可以自主。
于是所有喀尔玛克的长者都谆谆告诫子孙:“不管身在何处,都要记得我们是信奉喇嘛教的喀尔玛克蒙古人!”
每一个流亡在外的子孙都做到了。
1917年,在俄国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喀尔玛克人被迫卷入争战。绝大多数的人加入了白军,与苏维埃红军展开长达两年之久的战役,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当白军战败,这批在俄国已经安家三百年的喀尔玛克人,又被迫流亡。
可惜,能够幸运逃离的,只有不到两千人左右,他们由黑海乘船逃到土耳其,再陆续逃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甚至远至捷克和法国,成为了真正一无所有的流浪者。
惟一能保留的,就是充满了信仰与自由的灵魂。
逃脱不及的那些喀尔玛克人,有的遭到杀戮,有的被强迫送到西伯利亚劳工营,一波又一波的整肃与迫害,不停地到来。虽然在1935年10月,斯大林为了笼络人心,批准了“喀尔玛克自治共和国”的成立。但是,到了1936年和1937年的“大清算”,数以千计的喀尔玛克人又被迫害,或革职入狱,甚至大批集体放逐到西伯利亚。
1939年,又一场让喀尔玛克人两难的战争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部分的喀尔玛克人选择相信苏联政府,相信这是一场护卫国土的圣战。于是,在1941年6月德国人入侵俄国的时候,他们奋勇抗敌。有学者在战后统计,认为在苏联的大小联邦中,喀尔玛克为“祖国”所付出的伤亡比例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喀尔玛克人选择了投效德军,想藉此向他们的世仇俄国作个了断。
【6】
父亲和我,就在佛堂所在的公寓里住了两个晚上。
父亲是长者,又是男人,所以可以在佛堂里搭地铺。而我和两个到德国来求学的喀尔玛克女孩子,只能睡在外面的小客厅里。
在这两天之中,丹僧叔叔和我说了许多话,又一次,他谈到了自己的童年:“我是1922年12月25日出生在雅茨库克的。7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为了让我上学,只好忍痛让我离开家乡参加一个儿童福利组织的教育计划。我和10个女孩、20个男孩一起,到首府附近的一个寄宿学校就读了好几年。
“1933年,是大饥荒的那年,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饿死在街边。我还小,食量也不大,只是觉得精神不好而已。但是,我们学校里已经有五六个孩子都饿死了,饿死的尸体都只能在匆忙中先拖放到另外一个房间。我因为昏睡不醒,也被拖放到这间房子里,就躺在十个左右裸体的死去的孩子之间。
“在这个学校里,有位18岁的大姐姐,她有个11岁的妹妹,平常就很喜欢同年的我,常常来找我玩。这天听人说我也饿死了,觉得很舍不得,就偷偷跑到这个房间来,打开房门,想在门边再看我最后一眼。
“想不到,我就在那个时候睁开眼睛,往四周看一看,就又陷入昏睡了,这个女孩奔跑着回去告诉她的姐姐,说丹僧没死,还活着。那时谁也不肯相信她。她只好哭喊着要姐姐一定过去看看。有位蒙古舍监听见她的哭喊,就过来探视,俯身聆听抚摸,想不到我果然还有呼吸,于是赶快把我移出房间,特别细心地照顾了几天,我就这样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其实,在那个年代里,喀尔玛克人真的几乎都是要靠奇迹才能活下来罢!”
丹僧叔叔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我赶紧问他,还记不记得那个女孩的名字?现在有没有再联络?
“我们又在一起读了3年书,1936年从学校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不过,我一直都记得她,她叫做布露葛尔,是个笑起来有两个小酒窝、眼睛很亮的蒙古女孩子。”
在58年之后,那个小女孩还活在丹僧叔叔的心中罢?不然的话,在提到她的名字的时候,他的眼睛为什么也好像有点亮了起来?
“1936年离开寄宿学校,前途无比黑暗。父亲已经在1933年的饥荒中饿死了,家乡还有姐姐和妹妹,我只好徒步去一个又一个的城镇里找工作,却又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我在德国和俄国的烽火线上做了好几次的炮灰!
“1941年6月当德国人攻进来的时候,喀尔玛克人确实曾有人拿起枪抵抗过,但是,当俄国军队重新夺回这些城镇之后,却又怀疑所有的喀尔玛克人都是叛徒与奸细。
“我不管谁是谁非,一心想要回故乡雅茨库克。找到了一个骆驼车,在酷热的阳光之下,路很长,没有水,可是还是给我挨到家乡了。但是,雅茨库克已经陷落在德军的手中,我算是自投罗网了。
“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德国人反而对我们很友善,他们把羊群和马群都还给我们,还宣布说如今既然已经脱离俄国的统治,我们喀尔玛克人应该恢复自己的宗教信仰。当时有5位喇嘛混在群众之中掩藏,听了这话之后就现身,领导我们在雅茨库克建立了一座佛教殿堂。其中有两位喇嘛是在多年前的‘十月革命’之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其中一位名叫阿格卓拉力吉,1891年5月1日出生,经历过许多灾难之后,终于在1941年回到故乡雅茨库克来。为了重建圣殿,他投进了全部的心力。
“1942年7月,我们在堪称华美的小小圣殿里举行了第一次的仪式,献上衷心的祈祷,渴望上天保佑,重新开始平安的日子。
“三个月之后,德军战败,美梦破碎。在俄国人与德国人之间,现在已经不需要选择了,都是曾经为重建出过力气的年轻人,如果留在家乡,只有等待死亡。于是,我们只能跟着战败的德军一齐撤退。
“那一年,我20岁,离开了我的家乡雅茨库克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7】
1942年的冬天,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一役惨败之后,撤离俄国。这时候,大约有五千名喀尔玛克子弟,因为害怕俄国人的残忍报复,只好与德军一齐撤退。但是,绝大多数的喀尔玛克人自认清白,他们从来不曾与德军有过什么牵连,就都留在家乡原地。
这些又一次留下来的“余留者”,想不到竟然与他们的先祖一样,又一次遭逢到含冤屈死的悲惨厄运。
1943年,斯大林复仇行动开始,他以“通敌”、“叛国”的罪名,加在喀尔玛克人以及鞑靼等5个小国人的身上,12月27日,宣布解散喀尔玛克共和国,再将全体人民集体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劳工营去。一去13年,漫漫长夜,无人问津,在13年之间,整个苏维埃联邦没有一个人敢对他们有任何探询或者声援的行动。
这个世界假装无知、假装无事,即使曾经毗邻而居也假装已经忘记了他们!
一直要到了1956年的2月,在赫鲁晓夫那篇有名的演说里,才第一次提到斯大林时代的许多残忍行为,包括对喀尔玛克以及其他几族的大迁谪和流放。
1957年,为了自我在政治上的利益,赫鲁晓夫假装慈悲地为喀尔玛克人翻案,准许他们重回故土。但是,能活着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只剩下6万多人,还不到13年前被放逐时人口的一半。
我认得其中的一位。有一年,在欧洲,他向我描述那在零下59摄氏度低温里生活的感觉,他说:“起初,寒冷让人疼痛。可是,又不得不继续在户外工作,久了之后,整个人变得失去了该有的重量的感觉,好像变得很轻很轻。”
多年之后,面对着我,劫后余生的他带着从容的微笑,仿佛描述的是他人的情节。可是,当时的痛苦要怎样努力,才能熬过来呢?
斯大林曾经公然残害了数以万计的喀尔玛克人,你可以说他本来就是个恶魔。可是,那些自认是英雄,自认是二次大战正义之师的国家——英国和美国又如何?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情势混乱,一部分的喀尔玛克军队,也想到了这其实是投奔自由的好时机。于是,他们的领导者与盟军代表商谈,当时的盟军笑脸相迎,并且保证只要他们肯放下武器,就一定负责带领这些部队前往自由的天地。
五千多人的军队,五千多喀尔玛克壮士,就这样手无寸铁地把自己交付到盟军手中,坐上安排好的火车,大家都庆幸终于能够脱离苦海了。
想不到,火车在下一个站的月台前就停住了。月台上站满了一排排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所有的喀尔玛克军官都被带下火车,就地枪决了,而五千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士兵直接用原车押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荒原,从此从此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
原来,苏联已经和英、美两国有了一项秘密的协定——斯大林要求,所有在俄国境内的蒙古军队,都要交还给俄国来处置。
明明知道这是陷人于绝境,英国和美国竟然也会应允,喀尔玛克人是被出卖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现在都还时时自命为正义化身的英国和美国,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一段丑恶的历史?
但是,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假装无知、假装无事,满身满心都是伤痕的喀尔玛克人却从来没有忘记过。
【8】
丹僧叔叔在佛堂外的小饭厅里,招待了好几位前来德国的喀尔玛克留学生晚餐。这些年轻人很有教养,对长者特别恭敬,也都不过是20岁左右的年纪而已。丹僧叔叔说:“这些孩子多好!在这样的年纪里可以专心地求学问,多让人羡慕!”
而丹僧叔叔的20岁呢?
我们围坐在他身旁,听他重述那在战火之中挣扎求生的记忆:“喀尔玛克人的骑术是一流的,在战争初期,德国军队也曾经要求过喀尔玛克人担任监视铁路和公路的工作,一有警讯,就可以快马追踪或者报讯。
“但是,在撤退的长路上,寒冬已经封锁了所有的一切,任是多快多好的马,也没有用武之地。所有的河流和土地都结冰了,德国军官一直催我们走快一点,却是怎么也不可能加快半步。
“有一天,部队正走在结冰的河面上,俄国飞机发现了我们,马上俯冲逼近,子弹一排一排地扫射过来,我们这些人只能拼命往对岸奔跑。那天天气非常晴朗,对岸树林里白桦树的枝子一层一层的原本清楚极了,可是在那一瞬间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听见头顶上飞机引擎巨大的噪音,子弹尖叫着掠过,还有人群的哀伤呼号,这一切都交织在我耳旁,恐怖与挣扎使我奋力往前奔逃,同时大声地呼念着大悲咒,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等到飞机掠过了我们,枪声暂时停止,我才恢复了视力,才发现刚刚还紧靠在左手边与我一起奔跑的那位蒙古弟兄躺在我身后的冰上,双腿染满了鲜血,正向我大声呼救;而右手边的那位德国士兵已经身首异处了。
“那位蒙古弟兄只有18岁,忍受不了疼痛,一直央求我们射杀他,我走过去把他抱了起来,放在马背上,可是,等到了对岸之后,他已经咽气了。我检视自己全身,竟然没有一丝伤痕,不禁跪下向上天叩谢,到这个时候全身才止不住地抖了起来。
“在我的童年时期,一位老姑母告诉我,遇到灾难或者危险的时候,要诚信念诵大悲咒就可以逢凶化吉,从此之后,我是深深地相信了!”
这是幸存者在发言,在向众人见证他的信仰。事实也由不得我们猜疑,在那九死一生的经历里,好像真的是处处有神迹,处处都有上苍的眷顾。
可是,那些没有逃过劫难的魂魄,又该怎么说呢?
【9】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劳工营里,聚合了850名喀尔玛克人。
说是“聚合”,是因为这里面除了包括丹僧叔叔在内的刚刚随着德军撤退过来的青年之外,还有另一批“资深”的流浪者。
这些人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25年前,在俄国大革命之后仓促乘船从黑海逃离了追捕的喀尔玛克人。1920年后有些人流亡在东欧各国,也建立了一些小小的家园,想不到这次随着战败德军的撤离,又被迫抛妻别子地迁进了这些劳工营里,意外地竟然能和从家乡逃出的年轻人见了面。
重新见到同胞,重新听到乡音,对于这些已经离开家乡有25年的喀尔玛克人来说,仿佛也算是一场悲喜交集的“团聚”了!
然而,这850个喀尔玛克流浪者,在那一刻里,其实都是无家无国无一处可以依归的游魂。喀尔玛克蒙古共和国已经被斯大林宣布解散,所有的同胞都被驱逐到西伯利亚,没有一丝音讯;东欧的消息也被封锁,那些用25年时间辛苦构筑而成的小小世界又完全破灭,天下这样广大,却再无一处可以去投奔的了。
战争结束,大家离开了劳工营,却也只能暂居在德国,等待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替他们寻找容身之处,几经交涉,才在1951年的时候,得到了几个国家的接纳。
其中有571名喀尔玛克人,在1951年12月到次年3月这段时间里,陆续出发到美国定居。其他的两百多人,有的去了法国,也有的选择继续留在德国。
【10】
40年就这样过去了。
“现在,”丹僧叔叔说,“在欧洲的喀尔玛克人,如果加上他们的孩子,还再加上1920年的时候出来的那些喀尔玛克人的子孙,大约有1500百人左右。从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一直到东部的保加利亚、捷克、波兰和南斯拉夫,都有他们的踪迹,有的地方人很少,只有两三个家庭而已,还是在法国和德国的蒙古家庭最多。”
1945年之后,德国政府对待这些留在德国的喀尔玛克人还算不错,帮他们找到工作,也配给房舍。丹僧叔叔就是在1952年分到了这间公寓的,1954年结婚后也没有再搬动。
丹僧叔叔在1953年底,已经有31岁,知道家乡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回不去的了,于是,就像有些单身汉一样,登报征婚。写信前来应征的这位德国女子,是位寡妇,有个小女儿,虽然并不能算是那些直接受战争之害的战后德国众多的战争寡妇之一,却也是个伤心人,名叫安娜。
两个人约好在慕尼黑火车站见面,第一次相见,几乎没什么话可说。后来,也许是感觉到了丹僧叔叔的诚恳,两人才逐渐交往,最后在1954年7月15日正式成为夫妻。
婚后,两人又生了3个小孩。如今4个孩子都完成学业,找到了工作,也成了家,都搬走了,只有两个老人依旧住在这里。丹僧叔叔说:“孩子们长大了就搬出去住,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唯一挂心的,就是将来我不在了之后,还有谁会来管理这间佛堂呢?”
佛堂所在地的公寓,虽然并不是国家配给,而是租用的,所以也搬迁了几次,好在还有政府津贴,一般的支出可以维持。但是佛堂内的一切设备却是靠德国朋友的捐助,而晨昏洒扫以及其他种种杂务的管理,更是要靠丹僧叔叔的全心投入了。孩子虽然也遵从信仰,但是还有没有热情与力量来追随父亲的脚步呢?
这一间小小的佛堂,靠着好几位喇嘛的带领,以及丹僧叔叔全心地奉献,就这样在40多年间,逐渐成为流落在欧洲的所有喀尔玛克人的精神殿堂。
丹僧叔叔为我展示了这个佛堂里最早的一位主持喇嘛的相片,他就是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名叫阿格卓拉力吉的喇嘛。是在1942年领导着丹僧叔叔这些青年,在雅茨库克建立了一座佛教殿堂的5位喇嘛之中的一位。
德军战败撤退,这5位喇嘛也跟着喀尔玛克的年轻人一起行动,在军队撤退的途中,照顾这些年轻人,并且为他们祈祷降福。但是,中途有3位喇嘛被俄国军队俘虏了回去,之剩下两位到了德国。其中一位在1951年陪着那五百多名喀尔玛克人去了美国,在纽泽西建立了第一座喇嘛庙堂,而留在德国的便是这位阿格卓拉力吉的喇嘛。他在1973年10月9日去世,享寿75岁。肉身火化。当地的喇嘛将骨灰撒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一条洁净的河流里,但愿魂魄能够回归故土。
“那年冬天,随着德国军队一齐撤退的时候,喇嘛其实和我们一样,都想着也许四五年之后,就可以重回家乡。谁会知道一离开就是这么多年,喇嘛已经故去了,我也老了。”
其实丹僧叔叔年龄并不算老,只是健康情况很差,大概是不适合做长途的旅行了。
1989年,辗转得到家乡的消息,家中只剩下两个妹妹。当然,下一代也还有不少的侄子侄孙。可是,属于他记忆里的那许多亲人,如今只有这两个妹妹还在世了,健康状态也都很恶劣,大概也不能前来探望他。
“你知道吗?我以前常常会做梦,梦里总是会回到家乡。但是自从得到了家乡的消息之后,好像连梦都没有了。”
【11】
1993年9月,第一届“世界蒙古人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有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两百多位代表参加。
在会场里,我遇到好几位从德国、法国来的喀尔玛克蒙古人,都是旧识,大家在蒙古国的首都相见,更是十分欢欣,忍不住互相拥抱。=是,接着来的,便是悲伤的消息:“丹僧先生在八月份逝世了。我们明天要去甘丹寺为他求喇嘛念经,你要参加吗?”
我当然要参加。但是,在静听喇嘛颂经的时候,心里想着的却是两年前的夏天,在千里万里之外的慕尼黑郊区那间小小的佛堂里,丹僧叔叔曾经告诉过我的每一句话。
这样就是一生了吗?
我与他相识不能算深,可是,在那年夏日两天的相聚之中,好像在向我讲述那间佛堂的历史的时候,丹僧叔叔也把他自己的一生都说给我听了。
甚至包括了他的渴望和梦想:“你知道吗?除了渴望回到家乡之外,我这一生还有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去甘丹寺朝拜,然后再到戈壁看日出。我们蒙古族说:‘在戈壁看日出,是人间天堂。’其实,我也去过一些地方,看过一些风景,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洲,也真有些壮观的景象。可是,我从来没去过戈壁,不知道这一辈子还有没有可能到戈壁去看日出,享受那身在天堂的滋味?我看,大概只能是梦想了罢!”
甘丹寺内香烟缭绕,古老的佛幡在岁月的熏染下,那颜色有着无法形容的华丽和苍凉,这就是丹僧叔叔渴望前来朝拜的圣殿。置身在他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境里,我默默向自己发誓,要把他说过的一切都如实地写出来。
这就是一个喀尔玛克蒙古人的一生。
(附注:本文内有关喀尔玛克蒙古人的史料部分,多有摘自海中雄先生1992年2月22日到24日发表于联合报副刊《历史上最悲惨的迁徙》一文,在此谨致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