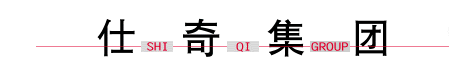“白毛女”成长记
口述/娜仁戈娃
整理/黑梅
听说了你们要来的消息我很高兴,这证明还有人记得我们,感谢你们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要死的人了)在文工团那段生活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我现在的眼睛不好,不能看书也不能看电视,现在我也八十多岁了,身体还不太好。你们能来听我说说往事,我也非常高兴。
说起文工团,我很激动,那是我失去的青春年华。提到“青春”这个词我有些伤感,这两个字让我回到无限美好的时光。让我回到了那个把我从一个无知少年教育培养成一名优秀的演员、一个共产党员的我的家——内蒙古文工团。
说到这,往事穿越时空,一下子展现在我眼前,内蒙古文工团的往事都展现在我的眼前,那些个人和事,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也立刻融入他们其中,回到青春时代。
说起内蒙古文工团,你们也知道,他是由两个小的文工团合并而成的,其中之一是成立于张家口的,以周戈为团长的内蒙古文工团,其中的大部分学员是内蒙古军政学院的蒙古族青年。另外一个文工团成立于赤峰的,布赫是团长。成员主要来至内蒙古自治学院的蒙古族有文艺爱好的青少年。
张家口的内蒙古文工团在国民党进攻的前夕撤退,经由张北、阿巴嘎、贝子庙、到达根据地林东。布赫同志领导的内蒙古文工团,在国民党进攻赤峰之前夕,1946年七月,我们演完《白毛女》之后,撤离赤峰。经由乌丹、新慧、奈曼、小河沿等最后到了辽西前线,就是现在的北票市。同年12月份,再行军撤离到当时的根据地林东。这样两个团就碰头了,然后就合二为一,过去两个文工团规模都比较小,合并以后队伍就壮大了。当时具体多少人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赤峰团我记得是22人,张家口团30多人,合并后大概有60多人。是一个大型的政治思想素养和艺术水平都比较高的文艺团体,和其他几个来自延安鲁艺的文工团站在一个台阶上,我们的队员起点都很低,为什么能站在一个台阶上呢,那是因为我们合并后有一个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很高的领导班子。
内蒙古文工团是第一个成立的民族艺术团体,党从延安派来很有水平的青年干部。他们是周戈,张凡夫、陈清璋、刘培新、沙青,张少科。这些同志,不但业务水平高,政治觉悟高,还像兄弟姐妹一样的爱护我们。
日本刚投降以后,我们赤峰那个文工团都是伪满洲国来的,根本没有“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没见过也不了解共产党。是那些老同志,特别是张凡夫,经常给我们上政治课,学习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精神讲话,学习整风文献,还经常给我们做政治辅导,使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宣传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过去光听反动宣传了,现在一看事实不是那样,再加上党对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思想觉悟很快就有了转变。
我们这帮人啊,都是热血青年,那么苦,那么难,每天吃的都是发了霉的小米饭,冻土豆吃到嘴里是辣的,都咽不下去。但是大家都很团结,很愉快,没觉得有什么痛苦,同志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张家口去的那个文工团条件比我们好,见到时他们穿的是藏蓝色的棉袄棉裤,还有皮大衣,而我们当时离开了队伍,找不到组织,已经12月份了还没有棉衣,每个人都穿着单衣服。后来实在太冷了,行军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破被子披在身上御寒。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卫生条件,被子是又破又黑,什么红的绿的紫的啥颜色的都有。从辽西前线回到林东都12月份了,零下30°摄氏度了我们才有棉袄。我记得很清楚,行军过河的时候,布赫的鞋湿了。我们当天住在了车马大店,他就把鞋放到了灶坑烘烤,想第二天行军的时候好穿,结果早晨起床发现有一只鞋的半个鞋帮烧坏了,没办法,他只好就穿那样的鞋继续行军,一直走到林东。那个时候思想教育特别严,一个星期就有一次生活会,大家要在会上做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汇报自己的思想。那时候我们都比较幼稚,有时候都是无限上纲,但是经过那样的锤炼,我们慢慢的都在成长,思想是在那个时候有了进步,人生观和世界观得到了提高。幼稚的事情我现在想起来还感觉有趣,那时候我们已经到了乌兰浩特,布赫的爱人珠兰刚生完孩子,她和我关系很好,她不知在哪给孩子弄了点牛奶,孩子喝剩下的一小碗牛奶就给留给了我,我也没有推辞就喝了。可就这被一个同事看到了,开生活会的时候批评我,“娜仁是资产阶级,还喝牛奶呢!”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批评和摔打当中,人生观、世界观得到了改造,得到了提高。在业务上,周戈不但是编剧、导演、他还是个演员。有这些老的同志的辅导、教育、培养,我们不但和这些团体站在一个台阶上,在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上,我们还有自己的优势。我们有很多是反映蒙古族生活的作品,这些在其他文工团里是没有的,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受到了当时东北局的重视,我们的常规剧目除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小姑贤》之类的戏外,还有周戈写的《血案》。另外,还有民族歌曲和舞蹈,我还在林东的舞台上用蒙语独唱过《诺恩吉雅》。我们文工团那时候除了有我前面说的那些老同志,还有著名舞蹈家吴晓邦,不但对我们进行基本功训练,还编排新的舞蹈教给我们,后来他曾经编排了一个蒙古舞参加过世界青年联欢会。
内蒙文工团那个时候的领导班子业务水平是非常强的。有我前面说的那些周戈,张凡夫,陈清章,还有布赫,那有一个画家尹瘦石,再加上这个47年来的贾作光,舞蹈家贾作光是吴晓邦介绍来的,刚来的时候虽然不是西装革履但也是穿戴整齐,头发梳得很亮,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中央专门叫我们内蒙的文工团来参加文代会的演出,我们在东北局排练了一个多月,就进北京了。我们的一场演出是几个舞蹈节目,每个舞蹈的前面要朗诵一首诗,也就是报幕词,解说一下接下来的舞蹈,这个报幕词是周戈写的我朗诵,我就是那个时候见到了周总理。总理问我:你是汉族吗?我说:不,我是蒙古族。他说,那你普通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在怀仁堂,周总理请我们吃的冰棍,当时人也不太多,那是我长那么大第一次吃冰棍,是鸳鸯冰棍,我现在还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周总理对我们的节目给了很多好评,那是内蒙古文工团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要求都很高,经常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也经常找谈话,组织纪律要求都非常严格。
内蒙当时有很多歌曲都是周戈作词,沙青作曲,他们写的歌在部队、军政学院广泛传唱。那些歌都非常的好听,“风沙滚滚,万马奔腾……”现在很多歌词我都忘了,但当时因为我们有自己首创的歌曲、舞蹈和戏剧,所以很受欢迎。这些节目都是我们团独有的,都是配合当时形势,配合当时走的政治路线,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面临两条路线的抉择,还有内容方面结合土改的,结合当时的政治任务,那时的演出很忙,这就是我们在内蒙古文工团的一段生活。
简单说了文工团的情况,再来说说我自己,论长相,论我的个头,我根本就不是当演员的料,结果我不但成为演员,而且是优秀演员,还红的发紫,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
那时候,参加革命的人少,参加革命的女人更少,参加革命有文化的女人少之更少。因为当时人们不认识八路军。那时候人都想中央盼中央,因为中央军是正统啊,日本投降人们就盼中央军来啊,都说八路军待不长,八路军是土匪,是小米加步枪,所以没人参加革命,但我参加了,我不但参加了还能念下来剧本,这样的人当时很少。还有我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还愿意蹦蹦跳跳,喜欢演出热爱舞台,我那时候是自治学院业余宣传队的,在《血案》里我饰演妹妹。晋察热辽军区组织五一演出时,我被选上去唱《黄河大合唱》,辅导我们唱歌的老师发现我嗓子好又能表演。就推荐我和其他几个人,参加晋察热辽文工团。1946年为庆祝党的生日而编排的大型歌剧《白毛女》,这是我首次出演“白毛女”。我们是白天晚上的排练,因为要赶在七一前排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都不是成熟的歌舞演员 一个个都是“生个仔”,我还不识谱。白毛女是歌剧,我要这一个月内把里面的歌曲都学会,那时候真的很忙,因为四幕剧比较长,喜儿由我和另一个人各演半场,或她演一天我演一天,当时没有麦克风也没有扩音器,全凭嗓子发声,一台戏唱完嗓子就哑了,你不使劲喊后面台子的观众听不见,你必须让后面的观众也听得见。我一般演前半场,因为我的个子比较小,喜儿一开场是小姑娘比较年幼的时候,她演下半场。
那时候我们排练还住在自治学院宿舍,有时候排练到两三点钟才回宿舍睡觉,早晨很多学员都走了我们还没有醒,所以当时我们在自治学院的影响特别不好,人们认为我们是二流子、不务正业,包括校领导对我们都非常有意见。排练节目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就从我们的头顶上过,飞的非常低,甚至能看到在飞机上把持机枪的人。当时承德已经被国民党占领了,而且马上要占领赤峰,可见当时那个紧张的程度,我们就是顶着国民党飞机的扫射和别人的不理解,抓紧排练的。因为年纪小,我的记性特别好,歌只要听两遍,跟乐器我就能跟下来了,但我也有唱不了的。我们团有个叫王艳磊的,现在已经去世了,后来他在包头文联当主席,我每天两三点钟回来,他三四点钟就叫我起来上操场,当时自治学院有个操场,我们俩坐在操场,他识谱,以前学过一些,她就一句一句地叫我,他唱一句我学一句,就这样把比较难的部分先学会。然后我再去排练。
最后改变自治学院对我们的态度的是因为我们所在的晋察热辽文工团专门组织了一次到自治学院的小礼堂演《白毛女》,让我演喜儿,从最初演到结束。一下子就把自治学院震动了,人们开始把我们当革命者看待了。
演完这场《白毛女》之后,马上就收拾撤退,因为国民党开始进攻赤峰。那段时间的生活是相当的艰苦,我遇见两次危险,一次是差点掉沟摔死,一次是差点脱离大部队走丢了。那年冬天的雪特别大,都没膝盖。在行军途中我又困又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有个叫高志一的在前面领着我。往前走的时候因为有个悬崖要拐一个弯,,可我睡着了还在一直向前走,多亏被他看到一下把我拉过来,他一拽把我拽醒了,我忙问他怎么了?他指着悬崖说,你看看,你要是掉下去还有命吗?我一看那大深沟,掉下去就完了,这是他第一次救了我一命。第二次也是夜里行军,因为那时候白天不敢走,有追兵啊。那一次,我和珠兰去解手。那时候,我们要把所有可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有两个裤衩也都穿上,有两条裤子也都穿上,一是为了保暖,二是为少背东西。所以,方便的时候一层一层特别麻烦。等我站起来在把衣服系好,发现队伍没了。哎呀,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恐惧是什么滋味,把我吓得腿发软,走一步就咕咚跪一下,四周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也静的一点响动都没有。我俩又不敢大声呼喊,怕被敌人发现,正好这个时候,还是上次救我命的那个人,发现我和珠兰其其柯失踪了,就留下来等我俩。结果就是我们三个脱离了队伍,上山下山,走走爬爬的。当时我们队伍有个木头车,车轮上有个铁弯头,磨得时间长了夜里走路会发出微稀的光亮,我们很远很远就看到那个光亮,我们憋不住就大声呼喊,组织也发现我们走丢了,也放慢速度等着我们。这就是两次遇险,后来高同志经常还逗我说救过两次我的命。
我从1946年开始演白毛女,一直演到1950年,从赤峰开始经乌兰浩特、扎兰屯、海拉尔、阿荣旗,最后那场在锡林格勒的贝子庙演。这场演完就算结束了,因为当时牧区是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但白毛女斗黄世仁是讲阶级斗争的,所以,《白毛女》这出戏就停演了,最后这一场我印象很深,当时有零下四十多度,白毛女不能穿厚衣裳,顶多给个小棉袄,最后到山洞里的戏还要光脚丫子,身上披着布条。表演过程中把我冻得够呛,一下台,就不管有人没人,赶紧去上厕所。光着脚丫子在雪地上,解完手再往台上跑。那是最冷、最艰苦的时候,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们在辽西前线撤退的时候,是边撤边宣传,搭台子演出,宣传共产党,宣传民族政策。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这都是我们的任务。内蒙古文工团的团歌里写着 “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名文艺战斗兵……”我们走一个地方就在一个地方演出,有时候都吃不上饭,就更别说吃肉了。有一个地方政府为了慰劳我们演出,杀了一口猪,锅里正炖着猪肉时说有敌人追来了,我们赶紧撤退,一口也没吃上,看着锅里咕嘟咕嘟炖着的肉,手又不能捧走,把我们馋的口水直流。行军走的脚都肿了,睡觉时只好在山坡上头朝下睡,每个人有一个小包放在脚底下,这样可以空一空。可常常是刚睡着就有人叫你起来,经常是多少天不脱衣服。
1947年冬天,我去呼伦贝尔纳文慕仁盟的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今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搞土改,那时候是武装土改,我们都有枪,我个子小,“大三八”我一扛就拖拉到地了,只能用“马三八”。后来我又得了一个“德44”式短枪。武装土改不像和平土改,我们每个人睡觉的时候都是抱着枪,开着保险。巧的是我们去区上开会的那天晚上,地主联军就去了到了我们所在的村子,他们扑了个空,如果我们在的话那后果谁也无法预料了,那时候的武装土改也很危险残酷,地主家都有枪。
我在文工团什么工作都做过,管过服装,做过机要秘书,我还写剧本,自编自演,我独唱,合唱,小合唱,大合唱,什么都干,我是文工团万金油干部,做什么都行,我还做女队的负责人。那时候,男队女队都是住集体宿舍,有的男女同志结了婚还都各自住在集体宿舍里,到了周末,他们才有机会在一起。这些事情还是由我协调、管理。在文工团,我没有没做过的工作,
我是1921年2月生人,1946年参加工作。当时只有15周岁,我记得我是正月17离开的家,从此一去没回头。 |